人类真的有这么不同吗?不同到必须要对“人”作多种不同的定义
去年此时(1993年),我正在筹拍(《独立时代》)这部喜剧小品之际,国际人权组织正要在维也纳召开大会,几个亚洲国家成员,包括中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国,基于文化立场不同的理由,联合要求大会修改国际人权宣言。当时这项争议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当然我也一样;甚至《时代》杂志都以此为题做了封面报道。从此,“新儒家思想”之名响彻全球,我这喜剧小品也因此急转直下,追根究底地深入这个主题。因为我发现我这个故事的一切细节,都是来自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对我而言,文化立场的不同只应该更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非更加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及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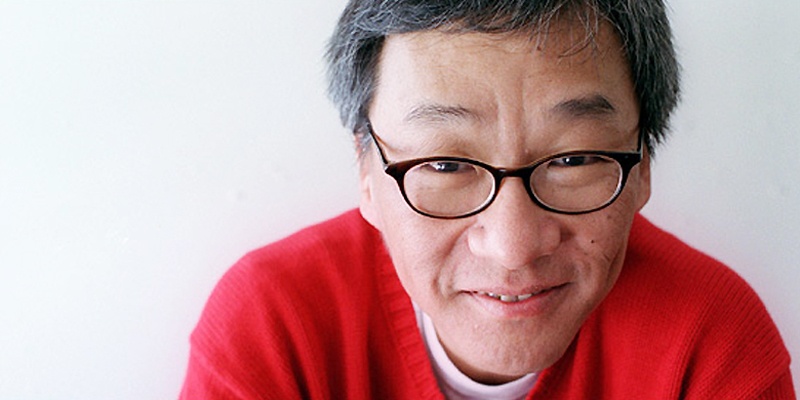 台湾导演杨德昌
台湾导演杨德昌对我而言,这项争议更明显地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我们东方人必须努力对自己文化的特殊倾向产生反省;同时,另一方面,西方人亦需立即对我们东方文化隐晦的部分,努力做深刻的了解。由于儒教文化的勤奋纪律,造成我们这些儒教社会过去十年来惊人的经济成长及财富累积,也因此改变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与东方原有的相对关系。这是自鸦片战争及殖民主义至今,这些儒教社会首度能挟持着财大气粗的自信,向西方社会毫不留情地分庭抗礼。西方在震惊之余,只有天真无知地接受这种新局面,甚至继续纵容自己一向的无知,几到可能被东方愚弄的地步。东西双方自我反省的努力必须是相互的,没有这种双方自我检讨的努力,一切文化的交流及沟通都将毫无意义。(《独立时代》)这部电影,代表了我在东方的这一半世界里,向这交流沟通的努力付出一己之责。
我们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历史教育课程里,甚至近期的一些中国电影中,苦难,穷困似是我们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在儒教教条之中,人民的富裕从来就不是一切训令的终极目标,儒教教条从道德出发,用同流,服从,纪律,个人对群体的牺牲以保障社会的和谐及团体的安全自由,极力包装中央权力核心的正常合法性。反讽的是,这些同流及纪律的素养,竟然造成了这些儒教国家这二十年间的经济奇迹及每年二位数的经济成长率。突然之间,我们被长久儒教教条训练下来的因循习性无法在儒教教条重找到任何指引我们如何去面对富裕物质生活的标准答案。在用尽了借自西方模式的既有工具(如民主政治)之后,我们不知道往前应该因循抄袭何种既有教条,来继续向前迈进。现在,也许我们能够大胆地向西方强权叫嚣要求修改人权宣言;然而,我们能够大胆的告诉自己如何走向未来吗?这种困惑已经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之中浮现了隐藏已久的潜在焦虑。
在我们强调整齐划一性的同流文化中,每个人最主要的生活目标就是“人缘”。若没有人缘,就可能有遭受到被别人摒弃及孤立的危险。然而,同流也暗示了一种虚伪。从小我们的教育就不断地官书我们如何做才是“正确”,任何个人独特的想象力及创意,都会遭受强大的排斥及否定,以致每个人都需要戴上假面具扮演一个别人熟悉的角色,来隐藏内心的许多感触,以免被怀疑为“与众不同”。因此,我们同时更相信别人都同样时时刻刻在装出同一副样子,隐瞒着他深藏不露的城府,使我们无法真正在群众之间建立最基本的相互信任。二千年来,假借孔老夫子之名而建立于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这种自相监视的预警系统,使中央权威有效地统治了这个幅员浩瀚的大国家。然而,问题是,如果一个文化无法自其社会成员中汲取,累积个人的智慧及反省,是无法去修正它过去的错误,无法评估它的现况,更无法远瞻它未来的需要。
 《独立时代》工作照
《独立时代》工作照没有个人想象力及创意的启发,一个社会的人性绝对无法透过艺术来得到肯定。因此,儒教社会中的艺术,除了有加强肯定中央集权核心的政治合法性的功能之外,别无他图,何况中央权力才是判决“人性”为何地终极主审。因此,在我们的文化里,艺术和政治宣传之间从来就没有明显的区分。这种偏颇的现象,被儒家“天人合一”的理论伟大的图饰。换言之,一切疑虑的解答,都能在每个人周遭的大自然中寻获,简言之,这一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这种没有问题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忽略所有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我们也同时放弃了一切自己未来的可能性。没有了帝王,我们推出一个独裁者来取代帝王;没有了独裁者,我们找个意识形态完全相同的国会来取代独裁者;政治宣言无效了,我们用商业广告取而代之。反正,无论如何,任何不经反省,不经检讨即能维持我们原有的相同外貌及相同思想的标准答案都行。
可惜,在今天生活的各个层面之中,我们所拥有的富裕,逼迫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切对切身前途的选择与判断。我们所面临的庞大挑战及困惑是不难理解的。孔老夫子若能及时投胎转世,像历史课本所述一样地来指点我们的迷津,不亦乐乎?而且我们还能借此机会问问他:这二千年来,我们是否有曲解他原意并以讹传讹地违背了他的教训?这样一来,我们也许终于可以不必只盯着别人彼此找茬,而让每个人都能自在地过自己的生活,作自己认为对自己最有益的决定。不论是在选择吃一份起司汉堡还是一碗牛肉面;还是在决定用针灸或是服用抗生素;还是投票给执政党候选人或投票给他采取同样政见立场的反对党孪生兄弟……
你可知道中文里没有Irony这个字?也没有Frustration这个字?所幸中文还是有一个人类共同的字眼——选择,Choice!这个激发鼓励人类个体思想及智慧的字眼,是我们的文化中唯一能带给我们对未来产生希望的概念。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我们”,迄今西方尚未有缘一识的我们那最隐私的一面。(《独立时代》)这部电影谈的是我的信念,不论最后我们赋予 “人”这个名词是何等地定义,我都深信我们都属于同样的人类。如果不然,我们又何必拍电影?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交流,国际影展还有什么意义?
杨德昌
写于一九九四年四月
赴戛纳国际影展竞赛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