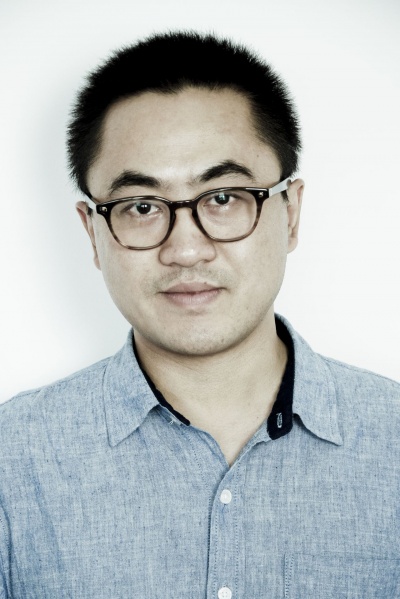 《亲爱的》、《中国合伙人》编剧张冀
《亲爱的》、《中国合伙人》编剧张冀张冀,湖南湘西人。早年曾做文案工作,后来觉得写字最赚钱就是做编剧,又看到不少同行不如自己,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个行业里了。后来才发现,“烂”编剧也不好当,只好坚持自修内功。后来跟人合作创作过多部电视剧,直到电影《中国合伙人》张冀的机会才来了,虽然那也是一部跟人联合创作的剧本。但电影《亲爱的》完成之后,张冀得到了陈可辛的认可,并公开评价他是一个能把很简单的故事讲得很丰富的编剧。不只剧本写得好,跟自己的品位也非常像,完全能写出他想拍的东西。这在编导关系紧张的今天,我们应该先给两位合伙人点个赞。
电影《亲爱的》是一部根据现实新闻改编的电影,编导有意回避唯一的罪犯角色,让活着的角色没有真正的坏人,多视角探讨生、养、情、法种种羁绊,抨击社会自私冷漠。故事没有落入俗套,感人而不刻意煽情,目前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那么编剧张冀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主题、人物以及故事的点点滴滴的,或许这篇专访对你创作会有所启发。
任何一个精彩的人物都有某种奋斗
记者: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个故事?
张冀:2012年,那时候《中国合伙人》拍完了,导演的搭档陆垚(他也是《亲爱的》联合制片人)跟我提到有这么一个项目,是关于拐卖儿童的真实案件,在媒体和公众反响都很大。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件事。他就把原型彭高峰的纪录片、天涯网贴还有原型的采访资料,都发给了我。我是在晚上看的,就睡不着了。后来又跟陈可辛、监制许月珍开了两次会,就定下来写这个故事了。
我想,首先这是个真事,真人把他的心路历程都完整写下来了,有底。其次,社会题材是我一直想碰的,同时又直觉地意识到,这个可以做成一个不简单的故事。
电影有三个属性,艺术性、娱乐性和社会性。我个人觉得,目前国产片所处的这个时代,娱乐性和社会性更重要,普通观众形容国产电影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好搞笑或是接地气。另外,我认为信息量大的文本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不仅是电影整体叙事,连单场戏信息也要达到淘宝的节奏,年轻人每天在网上买进卖出眼花缭乱春城无处不飞花,他们眼里的世界是碎片的、混搭的、即时变化的,这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审美。而这个故事我认为它天生具有大信息量,完全可以提速。那如果是普通伦理剧,到60迈就发飘了。
记者:这个剧本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张冀:一是当真事变成电影,戏剧化的度如何掌握,怎么不去破坏写实的自然,但又要增强观赏性。二是容易逃不出伦理剧的窠臼,陷入煽情的套路。 三是我没有孩子,缺乏生活体验。说实话,接这个对我来说是有些冲动的,这仅仅是我写的第二个电影。
 《亲爱的》剧照
《亲爱的》剧照记者:电影里赵薇所扮演的李红琴这个角色比较复杂,她即是人贩子的老婆,又是一个悲剧角色。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吗?还是在后来慢慢成形的?
张冀:有真事是开了个头,但工作才真正开始。首先你必须挖掘适合你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再去描人物,搭结构,有时候人物和结构要交错来写,互增有无。最后形成第一稿大纲。
现代社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同阶层是一个大一点的孤岛隔着另一个大一点的孤岛,大家拒绝沟通,有时还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想象对方。但电影的好处就是它能让剧中人和解,也许是想象的和解,或是意象的和解,竹林风过,两个人默默无言,却听懂了彼此心里的苦痛都是一样的,这才是人生。李红琴是这群孤岛中最卑微最沉默的一座,是被侮辱被伤害的底层女性,她的悲剧根源不是人性恶。如果还把她写成一个恶人,那十九世纪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就都白写了。
如果说李红琴有什么设计的话,我认为,任何一个精彩的人物都有某种奋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跟人物无关,关乎的是主题。艾伦·索金说,当你描写一个反英雄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就是坏人,而是给他设置障碍。
记者:你接触过李红琴的原型吗?把原型变成故事的角色,这过程需要下什么功夫?
张冀:没有。我认为资料已经很详实了,该跟原型保持距离了。距离是造梦的条件之一,有距离才会冷静地看到全局,看到每个细节在全局中的作用,再好的细节跟主题无关都赶紧删掉吧,即便拍出来了也逃不过剪辑师的刀子。
原型变成人物,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你的主题,主题有千千万,但最适合你正在做的这个剧本其实只有一个,找到了以后,所有人都得为它服务,必须养成对这个的强迫症洁癖,要上瘾。我说的不是要主题先行,比如一个哲学的概念,而是说故事主题。一个人的孩子丢了,他终于找到了,但他的儿子却带回来了另一个妈和一个妹妹,这个故事是前提,但它有无数主题的可能性,你要选出一个最准的主题。
 《亲爱的》剧照
《亲爱的》剧照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讲成一个单纯的伦理剧,爱恨情仇,破镜难圆,这个我本人完全没兴趣,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你可以讲一个批判戏,传宗接代文化是悲剧根源,看起来好似能深入,但其实是条走不通的老路,一篇网贴都能比影像讲得好看。你也可以经典现实主义,表现男主人公田文军的自省和宽恕,一个人自省往往是因为痛苦,这个可以有。那宽恕呢,他宽恕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人性善吗?我认为人性善只能做到不恨,而宽恕则是要超越到形而上。田文军不是《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李红琴也不是马斯洛娃。这个绝对不能骗自己,骗自己就是你逼着自己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你就只能编出谎话。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借这个事件,去描写一个转型社会中不同人群的众生相,他们的抗争与和解,但是你越努力,你就会发现越多真相的复杂和命运的荒谬。
另外,原型变成人物,我尊重麦基的《故事》里说的方法论,人物的戏剧行为和他的内心渴望是有层次反差的。根据这个方法,我一早就设定了李红琴的表面行为是她为了要回女儿去找律师打官司,但她内心的渴望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因为不能生育的女性在农村是受尽歧视的。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她,这是全片最荒谬的一个情节。从命运而言,人的抗争最后都是无意义的,只能带来荒谬感,但毕竟人性的坚持留下了一道光芒,一道光就足以照亮一团黑暗。这就是我心中的李红琴。
记者:当李红琴在影片最后看着肩上扛着孩子的田文军,说,“别给他吃桃子,他会过敏。”这一刻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在两个家庭里都建立了一种情感的关系,整个电影在此刻对拐卖儿童这个事件的思考也升华了。像这样感动且发人深省的戏点,您觉得作为一个编剧,如何去经营?
张冀:这个前后呼应的技巧,是常用的经典剧作技巧之一。原剧本中并没有这个,黄渤进组以后,针对他这个人物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我就给他增加了一场面对DV寻人启事的戏,台词有一句,请买了孩子的人不要给孩子吃桃,会过敏。拍到后期,导演说要加一场黄渤和赵薇的对手戏,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导演还有所有演员,赵薇黄渤郝蕾大为,好像张译和张雨绮已经离组了。大家就觉得这场对手戏少一句对话,戏眼那种。讨论了很久,最后陈可辛公司的香港编剧陈嘉仪,她是来探班的,她灵机一动说,不如也说桃子吧。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说,碰上牛逼的戏,编剧一定要跟组,有些好东西不是键盘敲出来的,是现场碰出来的。
记者:无论是李红琴,还是田文军、鲁晓娟,可以说这些角色如有一个失败了,都可能造成整个电影的感染力下降。不知道你在创造这些角色的时候,对哪个角色用情最多?又是哪个角色最不好写?为什么?
张冀:用情最多是李红琴。最不好写的是田文军,因为他没什么特点,你没什么直接的技巧可用,实在是难办。如果这个人太有特点了,最粗暴的举例说他断胳膊断腿什么的,可能会煽情,但其实会让观众难代入。
 《亲爱的》剧照
《亲爱的》剧照记者:相对于电影的前半部分田文军寻子,后面发展出来的李红琴争女这部分,有人说戏剧性更强,却也有点不符常理。当然看法也是因人而异。那么,在一部现实性强的故事里,如何平衡故事的真实性和戏剧性?
张冀:故事是真人真事,但几乎所有情节都是虚构的。虚构就是在做戏剧性处理,或是加强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前半部就是这么做的。后半部戏剧冲突更大,人物都卷进来了,难度也更大了,雕饰的痕迹容易让人看出来。写实是这部戏的整体基调,必须要保证,那刻意的情节就删掉,或者把它们改一改,掩饰住技巧的部分。还有就是依靠演员的表演,有些类型,剧作要压住演员,大胆上技巧,机灵一点也不怕;有些类型比如写实的就要稳住,关键是不能写跑,要大度地给演员发挥空间。我觉得合作的基础是大家都要对自己有自信,也就能看到全局之下自己工作部分的功能。
为了整个戏的写实感,很多技巧不敢用,也不能用,这是很痛苦的,因为功力不至,还没到那种不写套路就出味道的能力。写戏,还是味儿最难,看起来没有技巧,却满纸戏味儿,实在是难。写戏,稍微对自己有点要求,就知道有多难。但这也算是动力吧,真正的快乐都是建立在痛苦之上。
记者:拐卖儿童这一犯罪行为有着很多案例,在把素材变成影视作品,这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或者作为一个编剧,您如何积累和处理生活素材?
张冀:首先是功力,也就是整体素养,要日积月累。保持阅读社科书、经典文学和各类电影,包括艺术片和好莱坞商业片,都得看。艺术片教会你格局和艺术视野,商业片增加你的技巧经验和敏感度。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一个有小三的女子自杀的花边新闻,他能写成这样,成为探讨婚姻本质和人应该如何去的伟大小说,真是高山仰止。其次,要从素材中找到主题,这个主题要配得上大银幕的放大,千万观众的检阅,要稳准狠,要敏锐。其三,技术上,有时候要加东西,有时候要减东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叙事主线更清晰。同样是素材量翔实,《亲爱的》这个剧本我其实一直在加东西,《合伙人》是一直在减东西,原因很简单,《亲爱的》原型素材离我要的主题还不够,《合伙人》相反。还有,我的体会是,往往小的就做大,大的就变小,但这只是规则,不是不可破的。
记者:陈可辛曾在一个采访里说,你写了一个让他非常喜欢的剧本,加了更多社会的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情况,而不只是打拐的事件,让他更想拍了。当导演有这样一个剧本,就会更有底气。那么,你觉得作为一个编剧,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现象吗?又应该怎样去反映社会现实?
张冀:编剧是最应该关注社会现实的,因为你面对的是最现实的观众。编剧一定要比作家烟火,作家可以只书写自己。我国古代那些写剧写章回小说的哪个不一身江湖气,对世态人情烂熟于心的。现在有互联网了,信息量是优势,但怎么都不如跟人面对面的接触好,人之间的气场,有一种跃然的灵感,扑在你创造的人物身上。
 《亲爱的》工作照
《亲爱的》工作照反映社会现实嘛,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多读书,多看高人的分析。那人家讲得比我们编剧牛逼多了,高人往往有对现实解读的独特角度,这个是比不了的。你有你的手艺,这是你的本事。比如说,中国现在是转型期社会,这就是个好的概念。我跟朋友说过,《如父如子》一看就是日本人的东西,处于平稳期的社会和普及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所能产生的电影。我们还是转型期,变化快,反把他乡认故乡,泥沙俱下,人群混杂,观念差异,地域大方言也多,就有一种荒诞感,这是宁浩成功以后吃得最准的地方。那《亲爱的》也是转型期社会的写照,你的故事必须反映你的时代,这还不是真诚,这顶多只能算是清醒。真诚太难了,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做到真诚。
其次,上网看看新闻,听各行各业的朋友聊天,也是可以观察到一些东西的。对观众则永远要保持警惕,取悦他们不难,寒碜他们也不难,难的是跟他们贴在一起,观众就像一个你不可能真正拥有的情人,他们能让傻子开窍,也能让聪明人变蠢。
记者:太有社会话题性的故事,处理不当的话会很容易滑向说教。你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张冀:说教是因为你在批判别人,如果批判自己你就不说教了。
记者:听说剧本第一稿,是场大的官司,赵薇打官司打赢,把女儿带回来养,然后才发觉自己怀孕了。后来为什么改了?
张冀:第一稿不是法庭戏,是在福利院由双方律师出面调解。然后过了好几稿,各方意见出来了,说高潮戏不明显,我就改了一个像好莱坞那样的法庭戏,女儿都给李红琴了。在这场戏拍之前,这场戏拍完没两天就杀青了吧,导演跟我说,他觉得这个戏拍到现在,非常写实,法庭戏好莱坞太假了吧,我就把第一稿给他看,他一拍大腿,说这个好啊,这个自然啊。生活就是这么荒谬。当然,后来还是改了改,比如法官不那么严肃,说话很生活化,没那么教条,还去接个水什么的,其实工作也很烦,楼道里永远充斥着诉讼双方分家产的吵闹,他揉脑袋什么的。
记者:从《中国合伙人》到《亲爱的》,你和陈可辛合作了两部电影了。你们一般是怎么讨论故事的?
张冀:我交出一个基本的东西,他就开会提意见。他一般比较务实,不说虚的。虚的我一般自嗨一下就好。他是领航,有经验,有见识,很开放,而且自带制片思维,让你在安全的航道里。陈可辛的生活中只有电影,还有他的家庭,我们要聊些别的,他就起身离去,回酒店游泳去了,不带走一片云彩。监制许月珍类似于剧本医生,她以前也写剧本,会帮我出招,修订人物,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合伙人》海报
《中国合伙人》海报写作可以让你跟世界和解,也能治疗心理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编剧这条路的?
张冀:我比一般人强一点的地方只有写字,以前我是个写文案的。写字最挣钱的就是当编剧,我就决定干这个了。我真正干这个,应该是2005年。
记者:您如何看待“编剧”这个职业?
张冀:苦。而且网络小说才是最挣钱的。要干这个,首先是技术,你都得会;其次是人生阅历,除了一些天才,基本三十岁以后才能写出一点味道;阅读,该读的经典都要读。最后,要能吃苦,要忍受寂寞,不主动参加文艺圈社交俱乐部,真没什么可聊的,都是操练舌头的,没几个对话的。快乐也是有的,写东西可以让你跟世界和解,也能治疗心理。
记者:在这做编剧的这几年中,有没有动过转行念头?有的话,是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
张冀:一直接不到什么活,因为不是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出身,反而比以前更穷了。至于坚持嘛,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我认识到原来编剧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时候我看有些电视剧,我就想就这水平,那我也能当编剧。但编剧根本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好多人进这行,都是被这帮烂编剧骗进来的。编剧是个体系啊,太难了,所以你得先去学吧,要学你就得坚持。我基本是自学,更花时间。有次跟赵薇聊,她也说她喜欢做演员,因为太难了,难才想去做。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编剧的行业地位?
张冀:处于维权阶段。行业确实不够尊重编剧,但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把剧本写好比什么都重要。我钦佩站出来替编剧说话的同行,有些权益必须靠我们自己争取。
 编剧张冀
编剧张冀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题材都能写的编剧吗?
张冀:我希望自己什么都能写,但还要多学习,功力有限。我不希望自己被局限,老写一种也挺没劲的。
记者:你既写过电视剧,也写过电影。所以,你觉得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有什么不一样?
张冀:电视剧是一周有七天大家都得过日子,电影是一天就二十四小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以前看过一句话,好莱坞电影是讲困难,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欧洲电影是讲困境,困境是不可能解决的。很有意思。
记者:如果让你写一个连你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故事,你觉得会写好吗?你是否觉得技巧可以弥补故事情感和人物建制的不足?
张冀:技巧最好是用来锦上添花,你也根本写不好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
记者:基本上创作者多多少少都会遇上写作瓶颈,如果您遇到过,又是如何攻克、迈过去的?
张冀:等。看电影,看书,或是去散步。
记者:那么,写戏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冀:在空中楼阁内扮演话事人,多少会忘了自己现实的卑微,有利于心理疏导。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张冀:陈可辛的下一部戏,仍旧是现实题材。还有一两部也在谈。
(转载自编剧帮第323期,文章标题:专访《亲爱的》编剧张冀:观众就像一个你不可能真正拥有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