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符号,隐喻
把寺山修司定义为诗人对于理解他的片子是必要的,他的半自传体长片《田园死者祭》(摄于1974年,以下简称《田》)就是一部成功的诗电影。想象,十五岁少年的自己和二十年后成年的自己并坐一处,纠缠着真实的过去和回忆中的过去,修司把自己的诗歌转化为艺术的另一种形式,诗歌与电影融为一体以探究时间的真相。《田》中经常出现的手表和挂钟的意象,其实也是诗化的载体,导演要寻找一个真实的,唯一的时间,这就是母亲苦苦守护的挂钟所敲打出的时间,然而时间的真相总是为每个个体经验所扭曲,而显示出各自的差异来,这就是少年向往的马戏团里每个人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物理学研究的时间概念和诗歌蕴含的时间概念在这里交汇,“假如你穿过百年的时间隧道,刺杀了你的祖母,那么你是否存在”。
 《再见,箱舟》剧照
《再见,箱舟》剧照并不只是在这部电影里,修司的诗人气质在他的每部电影都浓酽般地弥漫着。在他的电影里,幻想和错位的现实交叉着,诗歌,符号和情节交织。看得出,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已经蕴含了内心世界的情感,复制一个外部世界,像纪录片毫厘不差地跟踪下来,那样并非难事,但是外部世界只是构成我们存在空间的一部分,难以展现的是一个人的内部世界,内外两个世界由诗意得以连接,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种诗意呈现在银屏上。作为早负盛名的青年诗人,之后的导演,寺山修司懂得如何掌控镜头与诗意之间的微妙关系。
除了诗歌之外,修司还嗜好借助符号来作为隐喻。挂在墙上的人像和涂写在白布上奇异的符咒,被抹成白色的人脸;《田》中的手表和敲响不止的挂钟,还有少妇的情人血液渗开在白布上,宛若一幅日本国旗,杂技团充气女人的需要打气筒的抽动也是对性的潜在欲念暗示,结尾一个手指指向和人们行进正好相反,它指着与“逝去”相反的方向;《上海异人娼馆》中“O”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洞口,一个无限扩张的包容空间,与之相似的还有O 记忆里的父亲把自己囚禁的方框,这些都是抽象的意象,具体的意象有O佩戴的鸟形状的戒指,各种形状的性虐工具;《草迷宫》中大大小小的手球,红色的长锦缎等等。
 寺山修
寺山修《抛掉书本上街去》中,哥哥领着受伤害的妹妹回家的时候,一个男子背着一具被解剖的猪胴体与他们擦身而过;《上》中,过气女演员陷入回忆而失控杀死了自己和客人,此时,一架钢琴漂浮在窗外的河面上,这些,都意味深长。
本民族的鬼怪传说也是寺山修司常常运用的符号之一。那些古装长发的红衣女子,挂在墙上的人像,让人们想起日本传说中雪女和河童的形象,《草》中那个被囚禁的女子千代女,她身上就有着雪女传说的影子。这些民俗符号的运用,充满了民族风情和哲学意味,足以让本民族观众来重审这些意象,也增加外国观众心理的神秘感。
不止是民俗的鬼怪传说,当代西方文化在电影中也是重要的构成。《抛掉书本上街去》集合了大量的波普文化:招贴画,摇滚乐,嬉皮士等等。日本在民族的眷恋和西方的诱惑中何去何从,对民族的反思写入了电影之中,两种文化的撞击,让日本无法置身事外而焦虑。
在本文的开头提到,寺山修司的电影是犹在祭坛,这个对原生风景怀着敏感和炽烈情感的电影诗人,把这种情感写进了他的电影中。田园,草地,雪山,废弃的铁路,往事和钢琴,交织在这个外部世界里,对于内部世界,他也致力于深处的挖掘,初看他的电影,总逃脱不开不伦之恋的萌芽。《草》和《田》中母子之间的暧昧情感,以及《上》中O因为失去了给他画粉笔框的父亲,而转向把这种自甘屈服的恋父情结转移到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史蒂文身上,以圆满自己需要强权控制下的归属感。这种“恋父”“恋母”甚至“恋子”情结放在电影里,不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的原欲(libido)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伊底帕斯情结的具象化吗?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来构成一个人的意识世界,几部电影中,《草》尤其在对被称为“超我”的潜意志世界的挖掘,并且将它以影象的形式展示出来,这并非易事。“超我”是一个可以被永恒探索的世界。因此这一类题材的电影多带有很强烈的实验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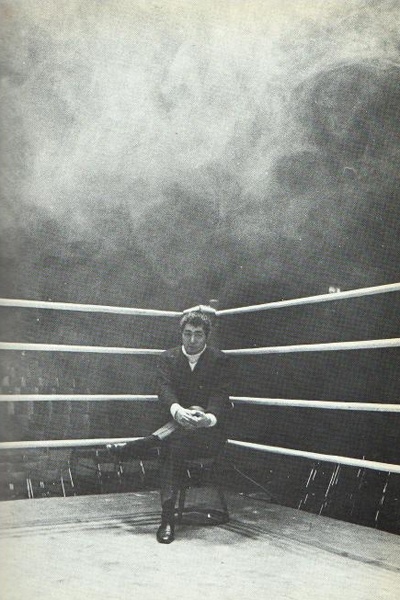 寺山修司
寺山修司
但显然寺山修司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意思的。我们看见,电影中出现的几段性事常常是处在绝望和挣扎之中,例如《抛》中妹妹被轮奸,《田》和《草》中被少妇和少年之间的性事,《上》中O被史蒂文强暴以及接客的情景,即使O与革命男孩的一段的笑声,也招致了男孩的杀身之祸。性本来是上帝为了让人类繁衍而提供给人们的快乐的诱饵,但在这里,却毫无快乐可言,性失去了它的使命,那么一切将岌岌可危。在他的电影中,性不但被种种符号隐喻着,同时性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隐喻。如果仅仅是为了释放感官刺激而费尽心思玩弄技巧,修司的电影就不可能被称得上艺术片,顶多是在日本泛滥的AV产品中玩得比较高级的。“性本能”和“生本能”(也是“死本能”)是人生的两大内容,修司把生,死,性三者穿插进自己的作品中思考,这也是很多日本大师的重要主题,和他同时代的不少日本导演,如今村昌平,大岛渚,也习惯用影像去反思构成本国民族性的生死观和性。在《抛》中有一个细节,一个人叫卖着“收购不中用的老头老太太”,他身后的板车上,绑着几个垂头麻木的老人,这种由于资源有限而对老弱者的残酷淘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这个水域紧锁的岛国,这个蓄意扩张的霸权民族,却诞生了这样一批悲悯情怀的大师,反思着个体的“生(死)”感与“性”感,透过个体关怀来关怀整个民族的命运。
然而,作为一个集大成的电影诗人,却未能假以天年。1983年,修司因肝癌死于日本,年仅47岁,之后的几年,他的几部电影陆续得到解禁,并在国内外发行。很难说他非自然的死亡是否和他的电影有关,也许是对人类绝望的挖掘和原生态的祭奠把他自己过早地牵引到那万物的渊源和归宿,一代大师终结于人类尚不可抵抗的绝症,幸好有电影,让我们知道他所留下的永恒的祭坛。
本文原载于《通俗歌曲》
【查看更多】
刻在祭坛上的电影:寺山修司的符号实验和颓废美学(一)
刻在祭坛上的电影:寺山修司的符号实验和颓废美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