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军队》是梅尔维尔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关于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的电影——1949年他的第一部故事片《海之沉默》(Lesilence de Lamer),和 1961年的《莱昂莫汉神父》(Leon Morin,pretre)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这也是他第一部和唯一一部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的电影。影子军队正好夹在梅尔维尔几部久负盛名的黑色电影当中,从更早的《第二口气》(1966),《独行杀手》(1967),以及之后的《红圈》(1970),《大黎明》(1972)。而与早期的战争片相比本片在形式感,故事性和哲学味上反而更接近这些作品。即使你不想下最后结论,但在今日许多人看来,影子部队是梅尔维尔最值得关注的电影——他的代表作——并且毫无疑问是六十年代最杰出的电影之一。
下面的访谈节选自《梅尔维尔谈梅尔维尔》,1971年由Rui Nogueira出版的一部梅尔维尔访谈录,转自朱黎伊的翻译版本,在外文原文基础上对之做了修改删补。中间括号内的文字是本文原作者附加的翻译资料。
对话双方:
采访人:RuiNogueira(以下简称R)
受访者:Jean-PierreMelville(一下简称M)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R:你是什么时候读到约瑟夫·凯塞尔(Joseph Kessel)的这本小说的?
M:我是在伦敦发现小说《影子部队》(Armyof Shadow)的,那是在1943年,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将它搬上银幕。1968年,当我告诉凯塞尔我的这个愿望终将实现时,他难以相信居然有人会如此执着地追寻一个梦想长达25年之久。
在凯瑟尔的书里,杰比尔相信自己会被射击队所杀,他在心里说:“我快死了……而我不害怕……那是因为我很擅长自我控制,就像动物一样地顽固。但是如果我真的不相信,直到可能的最后一刻,直到极限的极限,我也许就永远不会死了,多伟大的发现啊!”梅尔维尔在片中用旁白的形式使用了这段话和杰比尔以及其它成员说的许多话。就像凯瑟尔小说里许多被借用的技巧一样。这些技巧影响了影子部队和之后一部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黑色电影的风格。主观时间的极大弹性,特别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使得梅尔维尔的电影,尤其是影子部队,在死亡的瞬间不仅可以保持形式上的精准抽象,还确实地捕捉到了人类心理的真实图景。
注:[本片改编自约瑟夫·凯瑟尔(Joseph Kessel)《影子部队》,原书1943年在伦敦出版,以作者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种种体验为基础。出生于阿根廷的凯瑟尔,父母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移民,本人在法国接受教育,既是一位旅行者,也是小说家和编剧(他以创作了路易斯·布努艾尔《白日美人》(Belledejour,1967)的原作小说而著称),而《影子部队》是这些多重经历的集合。“每个细节都要无比精确,同时,任何地方都不可以与现实对号入座。”凯瑟尔在本书的前言中如此写到。换句话说,虚构——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被运用在了报告文学中。在Rui Nogueira的《梅尔维尔谈梅尔维尔》一书中,导演说他把凯瑟尔的方法当作了自己全部作品的指导原则。他曾换了一种说法对Nogueira解释说:“我的电影中那些人们通常认为中是空想的地方很多都是真实的记忆,是我走在大街上或是和人相处时注意到的事情,其实,我对展现自己真正的经历抱有莫大的恐惧。”电影制作者真正的意图以托辞和保密的形式艺术般地隐藏在人们的猜测之下,无论是在强盗片还是抵抗运动里,都伪装成了角色的生死问题,故事构造方法的同一性和《影子部队》里的杰比尔(Gerbier,利诺·凡杜拉饰)和《红圈》里的科里(Corey,阿兰·德龙饰)般差异性巨大的角色行为的一致性营造出了覆盖所有梅尔维尔电影的强大情感共鸣和深深的忐忑不安,但《影子部队》和之后严肃的黑色电影最大的优点还是在于其惊人的精密,抽象和简洁,就如一盘盘完美的国际象棋。
R:你十分忠实于凯塞尔原作的精神,同时你也拍摄出了一部非常个人化的电影。
M:在这部影片里,我第一次将那些自己见过和经历过的事情展现出来。我所展现出的那种真相,当然,是很客观的,可它与所谓的"真正的事实"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往往会倾向于记住那些合乎我们心意的事情,而不是那些真正发生过的。凯塞尔的小说写成于1943年的那个严峻时期,它与我在1969年拍摄的影片当然还是很不相同的。他在书中所写的许多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现在却不太适合用在现在的电影中了。根据这个关于抵抗运动的悲壮故事、这部关于抵抗运动的优秀文献,我创作出了这样一部回顾往事的梦幻般的影片,它是一次充满了怀旧情绪的朝圣之旅,带领着我们重回那个深深刻入我们这代人心中的年代。1942年10月20日,那时我25岁。我从1937年10月底开始当兵,从此度过了3年的军旅生活。其中一年我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另外两年则是在抵抗运动的斗争中度过的。请相信我,这段经历塑造了一个人。战争年代是不堪的、恐怖的,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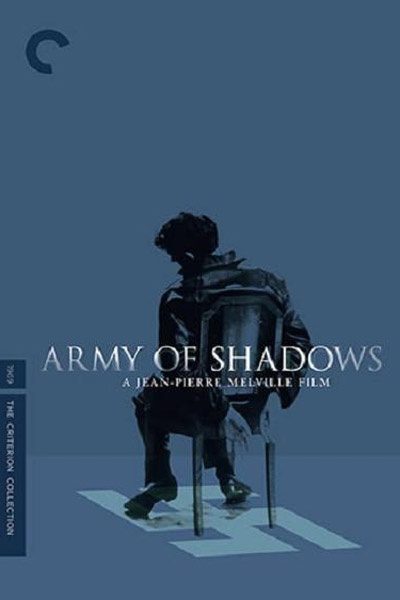 《影子军队》CC版海报
《影子军队》CC版海报注:不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梅尔维尔这一代人而言当然有着重大意义,梅尔维尔在1937年,二十岁时被征召入伍。他出生于犹太家庭,青年时将自己的名字从戈巴克(Grumbach)改为他最喜欢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记》的作者)的名字,或者像他对Nogueira所说的,因为他以梅尔维尔这个名字获得了军人勋章,所以战后他依然保留了这个名字。据Ginette Vincendeau——仅有的两本深入研究梅尔维尔的英文专著之一《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作者,另一本是Nogueira所著的现已绝版的长篇采访——所说,梅尔维尔大约在1941至1943年间加入抵抗运动,并在西班牙被捕入狱,而他的兄弟在尝试接触他时被杀害。(他们一家是犹太人啊!)1943年他在北非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虽然他参与过“自由法国”这点毫无争议,但是有些人,包括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曾导演过《铁皮鼓》(DieBlechtrommel,1979)】——曾经做过梅尔维尔的助理导演--都对他和“抵抗运动”的关系表示过怀疑。
除去个人化的标签外,在情节,角色,对白和内心独白的设置上,梅尔维尔的电影力图忠实——虽然更为简洁——改编凯瑟尔的原作。但是与凯瑟尔不同的是,后者毕竟是在战争似乎已有获胜希望的伦敦完成本书的,所以设置了一个开放,甚至可以说是有谨慎乐观倾向的结尾,而梅尔维尔站在二十年后的位置,清醒地看到大部分他将之作为电影角色原型的“抵抗运动”战士们都在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如何帮助自己的祖国迎来解放就被杀害了,所以他拒绝让任何一人逃出生天。
R:“痛苦的记忆!但我依然迎接你,因为你是我失落已久的青春。”《影子部队》就是从乔治·科特莱恩(Georges Courteline)的这段话开始的,它是否也反映出了你自己的想法?
M:的确是。我喜欢那一段,我觉得它格外真实。在参军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倍受折磨。我发现,想要相信一个人能像科特莱恩在《当兵的快乐》 (Les Gaietésdel'escadron,1886)中描写的那般机智、聪颖与敏感是很困难的,因为科特莱恩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也过得很不愉快。然后有一天,我思考着自己的过去,忽然明白了那种“不愉快的记忆”所蕴含的魅力。随着我的成长,老去,我慢慢带着怀旧情绪去回顾1940年到1944年的 那段日子,因为那是我青春的一部分。
R:我相信《影子部队》已被人认为是抵抗运动成员所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
M:《影子部队》这本书是关于抵抗运动的:它是所有关于人类历史上那个悲剧性代的文献中最伟大的也是最全面的一部。可是,我并不打算拍摄一部真实记录抵抗运动的电影。所以,我完全丢开了写实主义,除了一个例外,即德国占领军。每当我看到德国人,我都在想,“所谓的日耳曼亚利安人神话到底在哪?”他们可不像你以为的那般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他们看上去倒更像是法国人。在我的影片里,我忽略了那些无谓的传闻。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R:你当时是否有一个专门负责德军军装的服装顾问呢?
M:我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得到了服装设计师歌莱特。鲍铎夫人的帮助,她对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在行。一天,我们在拍摄枪决的那场戏时,担任技术顾问的法军上尉对我说,党卫军军装有些不太对。于是我叫来了服装顾问鲍铎夫人,上尉对她说:“夫人,我是阿尔萨斯人,在战争期间,我曾被迫加入了党卫军。因此,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党卫军成员总是在他们的左胳膊上佩戴一个袖箍,上面标着所属部门的名字……”“不对,先生,”鲍铎夫人回答道,“你当时多半是在作战部门,可是我们影片中表现的是党卫军的后勤部门。”于是,上尉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R:在法国,一些影评人指责你将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描写成了强盗电影中的人物。
M:那些说法实在是愚蠢透顶了。我甚至被人指责拍摄了一部戴高乐主义影片!更荒谬的是,有些人还试图从这样一部并未支持任何观点的电影中找到所谓的"最小公分母"(本质的立场)。可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很抽象的。所以,滚你的吧!25年来我都想要拍摄这部影片,无论什么理由我都可以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注:影子部队首次在法国上映是1969年秋季,情况糟到几乎不能再糟。所有重要的法国评论媒体,包括其中最具权威的电影手册 (Cahiersdu Cinema),都蛮横地把本片视为对戴高乐将军(Charlesde Gaulle)的刻意美化,这位法国总统,因为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对学生运动的背叛而受到众人的鄙视。只有少数一直看不惯电影手册精英霸权主义的电影学家如查理斯·福特(Charles Ford)等人才盛赞本片,并称梅尔维尔是当代法国最具作者气质的导演之一。但事实上,戴高乐在整个法国抵抗运动中只是边缘人物(只对国内而言确实如此),而梅尔维尔更是用反讽的手段把“戴高乐式的英雄主义”在战争使人处于极端状况时将经受不住考验的观点清楚表现了出来。(例如结尾女革命者的动摇)。在法国新浪潮的极盛时期电影手册对美国艺术院线的老板和发行商们存在巨大的影响力,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本片在美国被忽视如此之久了。在九十年代中期,无论如何,电影手册终于对梅尔维尔来了个全盘翻案,特别是《影子军队》,由法国studiocanal公司对原始的35毫米胶片进行了修复,并由在文艺片发行上经验老到的rialto影业负责本片在北美地区的发行。
R:那些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成员非常喜欢这部影片,不是吗?
M:对,我收到了许多离奇的来信,当我为22名最核心的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安排了一次私人放映时,我看到他们是何等的感动。他们都是杰比尔、雅尔迪(Jardie)、菲力克斯(Félix)式的人物。亨利·弗莱内曾经对我说:“1941年12月,作为战斗部门的领导人,我不得不回到巴黎,仅管我根本不想看到占领期间的巴黎。当我在星形广场站下了地铁,向出口走去的时候,我听到了头顶上行人们的脚步声。我惊奇地发现,我自己的脚步也开始和这种有节奏的声音保持一致。当我来到香榭 丽舍大道时,我看到德军静静地列队走过,突然,士兵们开始演奏音乐。你在电影开头的第一个镜头为我重现了这个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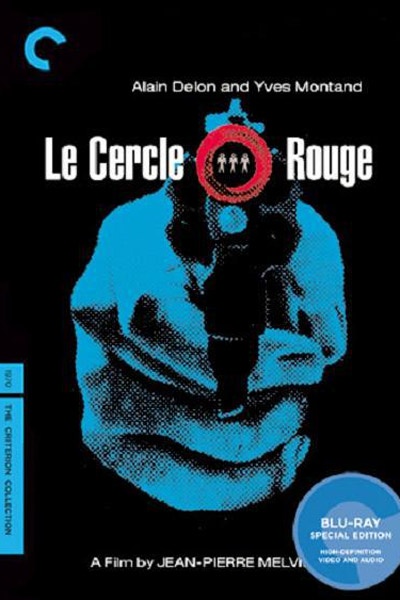 《红圈》CC版海报
《红圈》CC版海报你知道吗,为了给那个场景配音,我使用了真正的德国人走路的脚步声。因为那种感觉是无法模仿的。拍摄德军列队走过香榭丽舍大道的那个想法是疯狂的。即使是现在,我都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去拍了这个镜头。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即使是文森特·米内里(Vincente Minnelli)的影片《启示录四骑士》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1962)也没有这样做过。因为在这方面有一个惯例,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就有禁止演员穿着德国军装穿过香榭丽舍大道的规定。曾有一个德国人愿花高价从我手里购买那段片子,因为在德国的所有拷贝里,那场军队行进的戏都是黑白的。
为了拍摄这个或许是法国电影史上最昂贵的镜头--它花费了2500万旧法郎。我最初获准在伊埃纳大街排练这场戏。凌晨3点,整条街道都实施了交通管制,完全由煤气灯照明,穿着军装的人们开始在街上列队行进。那是个梦幻般的场景,就像瓦格纳乐剧的场景一般令人震撼,那种效果实在不是电影所能表现的。我敢对你发誓,我被它征服了。随后,我开始担心……我想知道当我于清晨6点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拍摄这个场景时,又会是怎样的情况。
在我一生所拍摄过的所有镜头里只有两个是我真正引以为荣的:这一个以及另一个我在1962年的《眼线》(Le Doulos)里拍摄的那个9分38秒的镜头。
R:你从哪里拍到影片开场的那个集中营场景的?
M:那是一个旧集中营,完全成了一片废墟,为了拍摄影片,我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部分的重建。就在这个破旧的集中营旁边,还有一个集中营,很新、漂亮、洁净,并且完好。后者比前者早建两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集中营,它令人害怕、十分恐怖。
R:为什么与书中不同,在影片里,吕克·雅尔迪和他的弟弟让-弗朗索瓦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秘密活动呢?
M: 这是因为我不想使影片成为滥俗情节剧。你没注意到么?也许你是对的。但是请到当地的电影院去看看《影子部队》吧。当那位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从潜水艇的扶梯上走下来,在观众认出他就是让-弗朗索瓦的哥哥的那一刻,他们禁不住喊出声来,“啊啊!”两兄弟无法相见使得一切更为突出,因为命运总是会把好牌洗乱这 一可悲事实。让-弗朗索瓦以Gestapo这一假名被盖世太保枪毙,他临死也不会知道圣吕克就是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而圣吕克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弟弟的下场。所有这些前提都能使让-弗朗索瓦的死充满悲剧色彩。
R:在影片中,为什么让-弗朗索瓦会给盖世太保送去告发他自己的匿名信?
M:这也是那些我从不解释、或者没有充分解释的事情之一。当菲利斯在马赛遇到让-弗朗索瓦时说道:“那么,你仍然相信巴拉卡?”当一个人拥有巴拉卡 (Baraka)[按照阿拉伯典故,巴卡拉是一种能给人带来好运的神圣恩惠]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难。让-弗朗索瓦去送这封会使自己被捕的匿名信时并不觉得害怕,因为他确信他拥有足够的巴拉卡来拯救菲利斯和他自己。但是,他却只有一颗氰化物——他给菲利斯的那一颗。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R:为什么让-弗朗索瓦与圣吕克要在图书馆中央的那个玻璃笼子似的地方吃那顿饭?
M:在战争期间,人们找不到煤来取暖,在巴黎,燃油也不是用来取暖的。因此公寓里冷得要命,那些房间巨大的老房子更是如此。于是,人们在房间里搭建起很小的木屋,他们可以在里面吃喝、读书,也可以更好地避难。在法国,当时的生活状况是无法想象的。人们经常穿着所有的衣服睡觉,鞋子和袜子也都穿着,因为除此之外 人们没有对付寒冷的办法。与此同时,饮食问题也不比取暖的状况好多少。饥饿成为了折磨,除此之外大家什么也懒得考虑。我还记得,曾经有一天我想方设法用腌肉和大蒜做了些三明治,我当时感到的那种快乐简直无法言表。在早晨,我们为了保持身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会喝一种用烤过的豌豆瓣煮成的水。由于我并不想拍一部关于战争的白描式的作品,所以在影片中没有去刻画这些细节。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自己对于那段往事的记忆与凯瑟尔的回忆渐渐交织在一起,毕竟我们经历的是同一场战争。在书中,就像在影片中一样,杰比尔这个角色其实代表了七八个不同的人物。集中营里的杰比尔代表了我的朋友皮埃尔-布洛赫,此人是戴高乐将军属下的前任部长。当杰比尔从巴黎大饭店的盖世太保指挥部逃跑时,他的原型则是戴高乐派的代表里维埃尔。事实上,就是里维埃尔本人给我讲述了他在伦敦的那次逃亡经历。当杰比尔和雅尔迪穿过莱切斯特广场时,他们身后的丽兹电影院外张贴着影片《乱世佳人》的海报,那时我想到了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给我描述的相似场景:“当法国人又可以去看电影,去读《鸭鸣报》(Le Canard Enchaine,法国一本以讽刺时事著称的老牌周刊)的那天来临时,战争也就要结束了。”
R:影片中的那个年轻人杜纳变成了一个叛徒,你对这一情节为什么不做任何解释呢?
M:如果对此做出解释,就会削弱背叛行为本身的含义。杜纳这个人太脆弱、太不堪一击了,他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卡斯特尔地区实施作战计划时的一个年轻联络员。
R:到伦敦之前,你在战争期间都做了些什么?
M:我当时是BCRA(即自由法国情报与行动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代办员,同时也是"作战与解放部门"的一名战士。后来,我到了伦敦。再后来,在1944年3月11日,准确地说,是在那天清晨5点钟我和第一批战友一起穿越了卡西诺下面的加里利亚诺地区。在圣阿波利奈尔,我们的行动被一名美军随军摄影师拍了下来。当我们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拍摄时,我居然还刻意在镜头前进行表演。那时,在村庄的另一边仍有德军活动,那不勒斯的广播里还在播放着哈里·詹姆斯的那首《小号狂想曲》。
我还是第一批穿着军装开进里昂的法国人之一。你还记得杰比尔与马蒂尔德在鸽子棚旁边会面那场戏的场景吗?当我坐着杰拉德·富尔中尉的吉普车到达时,那个鸽子棚就在那里,在属于主教管辖的弗尔维埃尔悬崖旁边的那条狭长道路上。在当时的里昂,德军依然到处袭击我们。我们在弗尔维埃尔的小埃菲尔塔上设置好侦察站后,于当天晚上离开了那里。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再见到富尔中尉(Faul)的吗?那时在1969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就是我拍摄德军列队从凯旋门前行进的那一天。当那个场景拍摄完成时,我和汉斯·波尔格夫一起走进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药店,汉斯在四年占领期间是大巴黎地区的一个乐队指挥,我把他从德国请来协助我拍摄凯旋门的这个场景,以前,他每天都要在德国部队的最前面引领队伍行进。当我和他在店里吃早饭时,不远处坐着一个看上去充满朝气的老人,我认出那就是富尔中尉,我在意大利和法国参加的所有抵抗运动组织的活动都是由他指挥的。25年之后,历史的车轮终于圆满的转过了一圈。
 《独行杀手》CC版海报
《独行杀手》CC版海报R:你在影片里添加了戴高乐将军在伦敦为吕克·雅尔迪授勋的那场戏,这是为什么?
M:因为在帕西(Passy)上校的回忆录里,有一个章节是描写给让·莫兰颁发解放运动勋章的。而吕克·雅尔迪就是以让·莫兰,还有其它人,为原型塑造出来的。此外,我觉得在影片里表现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其私人寓所为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授勋这一场景挺有趣的,就好像完全忘记了他们重返法国时将会面临的危险。
R:伦敦的饭店房间这个场景是否让你想起什么特别的事情?
M:这是一个精心重建的旅馆房间,那时每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法国人到伦敦执行任务时都会住进这样的房间。这意味着后来每当我遇到一位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时,对方都会问我是怎么找到他的房间的。
R:在影片里,我们看到由吕克。雅尔迪写的一本书,那本书实际上是另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写的?
M:对,那是由卡维莱斯写的,他是一位哲学和高等数学教授。他被德军处决了。当我将这本书重新标上吕克·雅尔迪的名字时,我保留了当初卡维莱斯所用的书名。书名《超限与连续函数》真的很高深,令人崇敬。
R:影片以对四个主角的死的宣告作为结束,这也是真的?
M:当然。像吕克·雅尔迪一样,让·莫兰在仅仅供出一个人名后被折磨致死,他自己的!由于他已经无法说话,盖世太保的一个头头巴尔比就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让。莫兰斯吗?”让·莫兰唯一的回答就是从巴尔比上校手中接过铅笔然后将名字里错写的字母“s”划掉。
为了拍摄一部关于抵抗运动和让·莫兰的真实影片,很多人都必须死掉。不要忘记,没有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比那些参与其中的人还要多得多。你知道在1940年底时,法国的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有多少人吗?六百人!直到1943年2月或3月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因为第一支法国地下游击队始于1943年4月。索克尔(此人 是外国劳工的负责人,就是他引进了强制劳动制度)发表了声明,命令将年轻人送到德国,这迫使大量的人选择了地下活动。那可不只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真的不是。
注:在最后一段,杰比尔再次,这次是和他的上司一起,吕克。雅尔迪(lucJardie)--这个形象部分来自传奇的抵抗运动英雄 让·莫兰(Jean Moulin)--决定必须杀掉他们的一位同志。但她也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暗杀结束后,梅尔维尔将剩余成员那一张张痛苦的脸庞展现给我们,然后穿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凯旋门出现在了画面中。数秒之后,一组简洁的字幕告诉了我们他们中的每个人最后是如何被德军所杀害的。人们通常希望像这样的电影中的一到两个画面能够在记忆中保存久,但是在看了影子部队后,我意识到,这部由凯瑟尔和梅尔维尔所创造的电影将会永远存在我的头脑里。
 《第二口气》CC版海报
《第二口气》CC版海报R:你认为这部影片得到了官方的充分理解吗?
M:这我不知道。我出席了一次在情报部举行的放映活动,地点是巴黎的一家最势利也最高档的电影院。在出席活动的两百人里只有一位抵抗运动组织成员,而只有他一个人在放映结束后还呆在座位里,没有离去。他的名字叫弗里德曼,就是他于1944年4月的一天夜里,在情报部刺杀了(著名的通敌者)菲利普·亨利奥特。
你还记得在影片《第二口气》里,利诺·文楚拉(LinoVentura)饰演的角色在抢劫后穿过铁道的那场戏吗?我们拍摄那场戏时,利诺对我说:“我抓住感觉了,梅尔维尔。今天,我就是古斯塔夫!”,“不,”我对他说,“今天,对我来说,你就是杰比尔!”之后我花了9年时间才说服利诺去饰演杰比尔个角色。当我们拍摄《影子部队》中利诺在那个早晨穿过铁道的那场戏时,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多做讨论,但是我敢肯定,就在那一刻,利诺正在回忆拍摄《第二口气》 的第一天时卡西斯铁道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注:尽管《让·皮艾尔·梅尔维尔》的作者Vincendeau指出关于梅尔维尔参与"抵抗运动" 的证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梅尔维尔的所有作品中再也没有一部如《影子部队》般拥有如此真实的体验感。与之相比,即使是他最为华丽和影响巨大的黑色电影——《眼线》《独行杀手》、《红圈》之类---看起来都像在扮家家酒。
这些作品自成一格但是并没有形成拜物式的自洽体系。(这种说法,当然只是相对而言。只有在比较了梅尔维尔的风格和昆汀·塔伦蒂诺之流的风格后,人们才会真正明白前者的作品是多么严肃!)梅尔维尔曾说:“所谓悲剧就像你身处一个死亡随时到来的黑帮世界或是战争般的非常时期。而影子部队的角色正是这样的悲剧人物,从一开始你就应该明白。”那些带着欣赏 浪漫英雄和在惊险的动作戏码中直达高潮的期望而去观片的人,必然会因梅尔维尔比动作戏更为精密的镜头处理和缠绕在个人和同伴间的悲观主义而大感困惑失望吧。)
本片叙事开始于杰比尔,一个国家工程师和抵抗运动的一个小分队的首脑……杰比尔在凯瑟尔的小说中是灵魂人物,片中最长一段的标题 就是“菲利普·杰比日记”,凯瑟尔把这个“第一主角”的声音分散到了其他几个角色中。梅尔维尔在这点上遵循了凯瑟尔的笔法,但是电影里的杰比尔成了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冷酷的角色,这要归功于文楚拉那标志性的细腻,理性而专注的表演。一贯表现硬汉形象,拥有强壮敏捷的身体和直来直去的砖头脑袋的文楚拉,这次用不断转动的头脑去判断一切。他是如何展现杰比尔思想上的强健的,就像所有伟大的表演一样,将会永远是个迷。不仅仅是他眼神的专注,说话的节奏或者声线的特质(梅尔维尔强调没有人教文楚拉如何调整声线,但他就是说得比任何人都更有说服力),而是他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好像填满了杰比尔的信息。梅尔维尔的绝招之一就是挑选并调教演员,但在他的电影中再也没有其他表演,包括让-皮埃尔·卡塞尔(文森特·卡索的父亲),西蒙·西涅莱,和保罗·克罗切特的精彩表演,能够像文楚拉的表演那般珍贵和饱含悲剧性。(梅尔维尔和文楚拉当时是对关系非常糟糕搭档,据西涅莱所说,拍摄时他们从来不会交谈。)
 《影子军队》剧照
《影子军队》剧照在关于战争无可逃避和吞噬个人命运的悲观看法上,2007年稍后上映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令人敬佩和感动的二战电影《硫磺岛来信》和《父辈的旗帜》与《影子部队》就有诸多相似之处。所有这些电影都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坏的境况下,人们还是会满怀勇气和尊严地采取行动,但事实上更大的悲哀却是只有战争才是如此珍贵的英雄主义的温床。权威影评人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的话也许最能够说明这部来自1969年的信使所具有的现代意义:“难得有一部电影,能将宿命重压下的希望在心灵中的地位体表现得如此准确。”
本访谈节选自《梅尔维尔谈梅尔维尔》,1971年由Rui Noguea出版的一部访谈录,转自朱黎伊的翻译版本,在外文原文基础上对之做了修改删补. 括号内的附加资料由bearbee翻译自amy taubin。他是《电影评论》(film comment)和《视与听》(sight&sound)的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