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的倒数第二个镜头,林家在知悉家中又多了一个二二八事件牺牲者后,行事如常,家中的女人,在厨房忙着准备饭菜;刚丧夫不久的大嫂吆喝着玩牌的大伙收拾,准备吃饭,此时主题音乐的前奏小心地潜入,配合着人物动作的节奏,将叙事画上句点。《风柜来的人》的最后一景是入伍前的岛屿男孩,踏上小木箱,在流行歌的播放中,大声叫卖削价的翻版录音带。《戏梦人生》结尾在悠悠的乐声中,呈现台湾人在镜头的远处忙着拆解坠地的美军飞机。
侯孝贤的电影总有令人错愕的结束。但这错愕并不令人厌恶,而是让人费解,像对拼图游戏的着迷,想一点一点拼出图案的整体。《戏梦人生》的结尾是个令人摸不着边的远镜头,观者必须配合李天禄之前面对摄影机的现身说法,才理解原来民众集体出动去拆解飞机残骸,是为了筹钱请戏班子演戏,敬谢众神。在这里侯孝贤以他喜用的换喻和迟延两种方法,点出了台湾民俗艺术与殖民历史之间偶然又必然的关系,也道出台湾人拐弯抹角地庆祝殖民统治的终结。《风柜来的人》到最后,一洗主角欲言又止的压抑,大嚷嚷的将原本对青春的窒愿和前景的未知,转为血气一掷的大拼博。这是侯孝贤一个突如奇来的扭转,和影片先前的节制收敛,大异奇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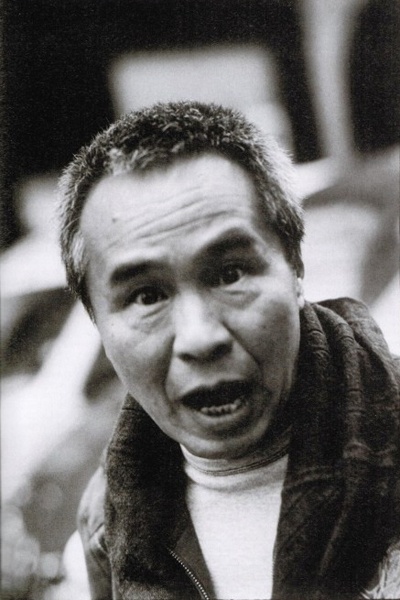 侯孝贤
侯孝贤电影诗学
从1980年的第一部《就是溜溜的她》到1998年的《海上花》(全数共十三部半作品),侯对电影诗学的掌握,愈来愈成熟洗炼。此处所谓的诗学,指的是在自觉的情况下,创造出的一系列电影表达方法。 这样的创作方式逐渐构成侯孝贤作品中固有的内在形式,此内在形式主要有三个部份,一是叙事的形态,二是作品基本的思想体系,三是调整第一及第二部份的反刍机制。要明暸侯孝贤电影,或者着手侯孝贤电影批评,都必须掌握这三个部份。先说叙事形态,侯孝贤的叙事形态包含至少四种要素(侯孝贤电影的分析通常需要多次阅读,因此此处所举的四个要素还不能算定数):构图、取景、摄影机的位置与移动、镜头的时间。
侯孝贤在「新电影」时期的第一部作品《儿子的大玩偶》中,便开始了他特有的冷静叙事形态。这个形态的有效形成涉及许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构图,包括(一)选景:譬如在《恋恋风尘》中代表反璞归真的自然风景,在《戏梦人生》中代表家庭的闽南居家建筑﹔(二)场景的布置:譬如以灯光设计、颜色来营造叙述的调子,以窗格、门棂、楼梯来制造多重空间;(三)非方法表演:以不指导的方式诱发演员「真实」的诠释。单靠构图并无法构成电影的效果,还须靠框景,才能赋予场景生命。这便是冷静形态的第二要素,即是对景框范围的取决。框景决定了该镜头的大小、深度和延伸性,譬如在《风柜来的人》中对人物位于高雄住处的框景,便清楚地表现该居室外的左右与对面等三面的空间深度。景框除了划清有形的叙事空间边界线外,也指涉线外的想象领域。
影评者喜欢使用「静态美学」来攻击或赞扬侯孝贤的电影。这点和静谥风格形成的第三点有关,即必须倚赖摄影机与人物、景色保持固定的长距离,和不常移动的摄影位置。这样的做法是将观者与叙事焦点的距离加长,使前者对情节的认知和认同缓慢,譬如观者在看到《戏梦人生》的最后一个远镜头时,一开始会觉得摸不着边,必须配合李天禄之前的叙述,才会明白过来。最后,叙事风格的成型也必须依赖较长的镜头时间,即长镜头,来增强构图设计的意义,和构筑远镜头产生的迟延认知。侯孝贤在每部电影里,总会以长镜头的设计和观者玩捉迷藏游戏。譬如在《风柜来的人》的打架一景中,我们先是看到一个男人和小童走进一条巷弄里头,朝着镜头较远一端的岛屿男孩走去。男孩们正和摊贩玩弹珠(赌香肠?) 。男人和男孩说了些话,之后两方就拉扯起来。就在冲突升高之时,双方人马往镜头的左边移动,出了景框。过了一会儿,打架又回到了景内,这样的叙事在镜头剪接之前重复了两次。同时,摄影的位置丝毫不变,限制我们只能看到镜头内所发生的事(或没有发生的事)﹕以不变应万变的摊贩,三个路过的阿兵哥,其中一人转头看向框外,彷佛对小小的骚动有着某种好奇。这个约莫三十秒长的长拍镜头设计使得观者必须等待、观察、并且以有限的视听线索重组这场打架事件。
以上谈的这些在通俗电影看来「无聊」、「不之所云」的影像语言,是侯说故事的惯常方式,但光有这些精巧的构思,是无法使电影产生更一进步的美学效果。诗学的另一个要件就是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侯孝贤电影总是有关日常生活、自然、周期、成长、祸害、打架、暴行、回忆、写作、技艺、政权、历史等文化中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母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日常生活仪式,在侯孝贤的笔触下,不仅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样子重现,还兼含文化、历史与政治的省察。这也是侯作品之所以无逾期限制,或不像许多非西方作品,必须负载越界所面对的「文化折价」风险的原因。侯孝贤谈到拍《南国,再见南国》目的之一,是想描绘台湾的某些世俗空间。这句精彩的话提供了解读的线索,我们可解释这是侯电影环球性与地域性的并存;可以说是发展国家对全球化一种有弹力的抗拒;也可以延引成是借着呈现台湾的「原创」空间,含糊地定义台湾无国籍的国籍性。
吃饭是另一个以日常生活来承载文化与政治的批判。《悲情城市》最后吃饭一景在布置上,和影片大部分的吃饭场景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仔细再看、再听,其实又有些差异。围着吃饭的三个主要人物,是老父、被刑求而残障的三子、和年幼的长孙。这三人的在场暗示他人的不在,包括女人与其它三个儿子的不在,女人的不在,因为这是父权结构下的家庭生活布置;其它三个儿子的不在,因为这是不同殖民势力对这个家庭伤害的结果。侯孝贤在准确地显现台湾汉文化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加入了他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海上花》海报
《海上花》海报品茗《海上花》
侯孝贤电影诗学的最后一部份是反刍机制。就像所有的艺术家穷毕生之力重复,修改,精练其作品,侯孝贤也惯性地反复他惯用的主题,再生他的技术,寻找新的创作意念。重复、再生、求变是诗学的最后一个要素:反刍机制。这个机制帮助侯检视先前的作品,并从此过程中寻找新的灵感。《海上花》被认为是侯孝贤别树一格的作品。侯离开了他熟捻的台湾社会和历史,走进了百年前的上海长三书寓,重塑韩子云/张爱玲笔下的妓院生活典章。除开这样近期台湾电影少见的题材外,《海上花》的电影语言部份看上去也大异于往。第一个出现的差异(或者可以说是创新)是以淡为主的剪辑方法。第二个出现的非侯孝贤叙事语法是较为贴近人物的摄影风格。如果我们仔细察看这些「新」技巧、「新」语法,则不难发现他们仍然保有许多侯孝贤电影诗学的原则。
先看淡的使用。全片扣除序曲和前后的工作人员表,约莫有四十个镜头。这些镜头以淡出、淡入作为剪辑或换景的方式。表面上看是急遽的改变,实际上在以淡作为剪辑/换景的过程中,有将近四成以上的景没有更改。这个情形在影片介绍第一位倌人沉小红和其领辖的的荟芳里时就出现了。这一段有关人物与情节的介绍共有三个镜头,分别是专事调停的洪老爷,为爱愁困的王老爷,还有另一陪客汤老爷,加上代表沈小红谈判的阿珠,这些人在荟芳里的厅堂中讨论着客人的责任义务。之后在一个淡出/淡入后,于同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坐在另一端的沉小红,这个镜头除了介绍正在哭的沉小红外,谈的还是金钱的事。在第二个淡出/淡入后,又在同一个厅堂里,我们看到罗老爷写局票,汤老爷坐一旁,见证王老爷替沈偿还欠债,之后又是一个淡,这才完成对沉小红和荟芳里的介绍。《海上花》的剪辑就循着这个形态进行,在每一个淡出与淡入之间,以一个镜头一个景的方式叙事,而且在每一个固定的场景中,镜头不会超过三至四个。这个观察可以归结两个重点,一、淡出/淡入的作用是在时间的省略、跳跃与延续的同时,保持了空间的一致,另一方面,也在空间的统一中,转回指向时间的进行。进行中的时间,固定的场景,不就是侯孝贤评论中,不管褒贬皆一致同意的「长镜头美学」﹖二、将同一景分成三至四个镜头来完成整段的情节,代表侯孝贤仍然偏好于以较少的镜头数目,5 有系统并且有规则地进行叙事,这和他先前的作品比较,并无太大偏离。换言之,在变换剪辑方式之时,就叙事形态和效果而言,仍重复其诗学的原则。
《海上花》的另一个明显的改变是贴近的摄影和较为频繁的镜头推移。侯孝贤在接受李达义的访问中,说到了摄影角度与距离的改变:
…从「风柜」到「海上花」我的转变是,从前以为镜头必须拉远一点,才能展现出一种俯视的,不带情绪的观照,到了「海上花」我发现其实不然,这种视角取决于你如何呈现剧中人,如果你自己在现场是非常冷静的、冷酷的,你喜欢他们、热爱他们,可以和他们一起但又有一双眼睛在一旁看着他们,即使镜头再近还是可以有那种效果。摄影机就像人在旁边,这个人就在旁边,他在旁边看着这一群人,有时候在这边看着这个人,然后那边有声音他才回过头去看,摄影机不可能像镜头转得那么快,它就可以慢慢的转过去,可能转过去时那个人又已经走掉或不讲话了,都无所谓…
这样的技法基本上可视为作者以较亲密的方式看待营造下的十九世纪青楼文化,但同时仍保有其自《风柜来的人》就开始的冷静凝视。但摄影的移动是不是就完全如作者所提示的,随着声音,人的走动,有意无意地捕捉人的活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多看几次」才能验证。仔细看了之后,我们发现人物走位、入镜、出镜等与动作皆与摄影机的定点或场景的空间设计有着必然的关系。以洪老爷为五少爷排解那个段落的两个镜头为例,可看出摄影对应着空间设计的精巧移动。在熟悉的淡入后,场景在周双珠的公阳里厅堂展开。首先是侍女双手持烟枪从厅堂外的楼梯上楼,摄影机跟着她的步伐,缓缓向内面推移,之后随着侍女的进入厅堂,摄影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跟随她的移动向
 《风柜来的人》日本版海报
《风柜来的人》日本版海报左横移,经过双珠,再到到五少爷处,就停住了。侍女为周双珠和客人五少爷上烟后,洪老爷抵达。洪老爷进入景框后,摄影应着人物从站立转为坐下的动作,重新框景。洪和五少爷说完话后,往周身旁的座椅坐下,摄影又因此动作重新框景。第二个镜头以坐在窗子旁边的五少爷开始,还是与上个镜头同样的景,差别在于摄影的位置往左前移了些,显露出厅堂的窗子和窗外的空间景观(一只挂在隔壁房间外的鸟笼,还有笼内吱吱叫的鸟儿)。就在镜头开始几秒的光景,从窗外望出去,看到双珠从邻室走来,经过阻碍视线的窗门,之后摄影机往右移,好容纳从外面进来的双珠,但是这移动仅到双珠先前的座椅处便停住了。双珠成功地按洪老爷的计策,说服双玉,为五少爷排除了麻烦。待双珠和洪老爷说完话后,洪老爷坐到五少爷身旁,为他解释一二。此时摄影随着洪的举动谈话,缓慢地往右移,将景框的边缘往右延伸, 好让我们看到此时入内的两名女仆。女仆为张罗吃饭而来,摄影机再往后推移,将此景的深度加大,好将在景框下方边缘的饭桌纳入景框里,以便让我们看到女仆上菜上饭的样子。这时候,事情告一段落,洪老爷移回他原来的座位,坐在双珠旁,等着吃饭,留下摸不着边的五少爷,继续困惑着。
从第一个镜头到第二个镜头,我们看到摄影机好象顺着人物的走动推移,并且在同一镜头中,由以往的不动,转变为数次移动。但从位置、移动的速度和方向来看,摄影机的运动仍然保持一贯的自制、冷静,在设定的范围内,界定人物与摄影的移动,以确保空间配置的一致与完整。所以侯所言的「旁观」、「冷静」、「冷酷」的贴近方式,不完全是摄影机自主的叙事,而是被静态构图牵制住的运动。譬如在第二个镜头,洪老爷的移动就设定在摄影机前后推移的有限范围内,让人感觉绑手绑脚,不是太自由。这一方面是景深不够(为了不破坏场景的密闭感,景深倾向浅些),二方面洪老爷的小范围「来回」也表现了三人既亲密又生疏的共谋状态。贴近摄影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少有的亲密,但这还主要靠密闭式的室内设计,不是自由的摄影运动。从这点来看,定点摄影还是侯偏爱的方式,这和先前的「台湾三部曲」和《南国》等作品比较,并无戏剧性的转变。这里我们看到侯孝贤在《海上花》中,遵循电影诗学的梗概:即程序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和故事题材脉络下,重复已定型的叙事形态,并且发展变奏。
除了以上举的淡和近距离摄影之外,《海上花》基本上仍以限定的距离说故事:仍然排拒以特写、零碎的剪辑来分割说故事的空间与时间;以迟延的方式交代事件/动作的因果:王老爷与沈小红、张蕙贞的三角关系要到王的践别宴结束后,我们才从已经易主的阿珠和洪老爷的闲话中得知;以有限的线索给予观者组织事件的由来:最后一景沉小红处的客人是新做的,还是原来的旧爱柳小儿?再生这些叙事法则的所产生效果和侯先前的作品一样,观者必须经过叙事时间与空间的迷阵,才能得知故事的发展。看侯孝贤电影可以用请客吃饭来比喻,主人将菜一小道一小道上,中间有短暂休息,好让客人细嚼慢咽,得以比较各道菜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大块肉大碗酒连连上,让客人吃在嘴里,看在眼里,筷子还不得休息,最后只得个鼓胀的脾胃。
结语:人本的神话系统
其实我拍片的过程,即是我学习及认识历史、生活、人的过程。——侯孝贤
历史、生活的最后归结是人。在许多的访问中,侯孝贤一再说,他的作品看重的是人;说的故事,以人为主。这个思想体系下的影像诗学形成侯对世俗的偏爱,影响侯对世俗超乎一般的想象、仿真、与润色。《海上花》也不例外。虽然侯孝贤这次退到很远的过去,迁移到离台湾较远的上海讲他喜欢的,关于人的故事,但对人的关注而呈现出的那些细节还是一致的。《海上花》讲女人,讲身在青楼却掌控权力的女人。放回侯孝贤作品的总揽中,他们是善于生存的人。人的生存是侯孝贤电影的基本神话,人为了生存打斗抵抗,为了生存背叛偷抢,也为了生存写日记、养育、游戏、吃饭,假如我们能一一想起侯孝贤电影的的每一个故事,其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行事。但在这次的故事中,侯孝贤和他的制作群对细节的修辞和装饰更为雕琢考究。从随片发行的两本图片书中8 ,可看出制片自我披露的意图,但更有趣的是这披露事实上是邀请我们一睹被侯电影语言隐蔽的金雕玉琢。《海上花》的世界不仅是历史的穿金戴玉,也是钜细翡遗的生活典章,更是人的娇癫痴怨、运筹惟幄。在侯孝贤本世纪最后的精彩演出中,人本的神话首次显现出封闭的困局。从荟芳里到公阳里到尚仁里到东合兴里,领辖的倌人好似楼宇内的美丽囚鸟,表面上拥有权力,但兜来转去,还是受困于长三书寓这个闭锁的妓院大家庭中,和这家庭内的规矩制度。故事因此在荟芳里的沉小红处,以吃饭的重复仪式(呼应前一个镜头/景的吃饭结尾)作为终结,点出了妓院生活的规则性,和无法偏离轨道的自我回转。
还记得马琳娜狄尔屈在史登堡的《上海特快车》中说的那句名言吗?『不是单靠一个男人就能把我的名字改成上海百合。』《海上花》中的上海之花也不例外,只是这次,他们不是实践好莱坞导演的东方情调,而是扮演者、重复着百年后台湾导演为女人讲述的故事。
本文原载于新浪微博
作者:叶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