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于传媒艺术网,有删节
作者:张也奇
张爱玲说:人生就是一袭爬满跳蚤的旗袍。而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的镜头下,光影忽倏交错,猛然的一漏光线,便将那华袍纤维隙缝间的所有不安、卑微、肮脏、却又生气勃勃的骚动尽收眼底。
镜头缓缓渐亮了,烟雨弄堂,每日上演着酒宴中的嬉笑怒骂;倌人与客人间的真假情谊纠缠着红牌倌人间的明争暗斗……一出出,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蒸腾着各人的欲望,算计,隐含不同的付出与结局……
镜头缓缓转暗了,散席了,安静了,歌舞升平的景况稍纵便成过眼烟云,唯有摇曳的烛光映照出古旧家具的昏黄影子,默然的回味曾经的繁华。于最低微尘土里生出的花 ,一开放,便失去了根,无所依附的在波涛中飘摇。
这便是当年在美国艺术院线上映时,被称赞为1998年最美丽的电影——《海上花》所讲述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台湾导演侯孝贤继《戏梦人生》之后,在电影美学上又一个重要的拐点。从题材上来说,这是侯孝贤第一次脱离当下台湾社会及历史的现实语境和时空背景,同时也是他第一次对古典小说名著进行改编,完全凭借想象构建出一个乌托邦般的19世纪末上海租界高级妓院的影像世界。从镜头语言上来说,侯孝贤结合影片的母题,开创性的将自己的镜头内部蒙太奇技巧集中而系统的贯穿在全片寥寥可数的37个镜头中,不仅创下了他至今所有影片中最少镜头数量的纪录,并完成了自《戏梦人生》开始的从静止远镜头到运动长镜头的镜像美学风格的转变。从作者的人文关怀来看,这亦是侯孝贤第一次如此集中和全方位的呈现女性形象。这里的女性形象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摆脱了之前侯孝贤电影中女性形象作为历史时空内男性形象成长的对应和陪衬的传统,凝视与怜悯着那些渗透莫可奈何的悲凉女性命运,真正提炼并展现出了女性无法言说的痛楚。而从摄制技术上,全部自然光源的运用和精丽的构图,行云流水般的场面调度,胶片曝光的成熟经验带来的油画般质感影像,被赞叹为“是朱石麟的《同命鸳鸯》(1960年)、《清宫秘史》(1948年),费穆的《生死恨》(1948年)以来中国室内剧电影中仅见的一部视觉上的杰作。”。从导演个人的创作轨迹上来讲,《海上花》作为侯孝贤执导的第十部长片,不但继承了标志其个人风格第一次转折点——《风柜来的人》这样人与历史时空的完美融合和独特的乡土气息中所传达出浓郁的家常氛围和人文关怀,并且进一步在镜头美学上探索,形成了独特的镜头内部蒙太奇长镜头美学,对后期的作品,如《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等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实为其早中期到成熟期的承前启后之作。
 侯孝贤
侯孝贤
一 侯孝贤的气韵镜头美学:自然,省略,写意
侯孝贤的影片一贯有着鲜明而独特的镜头风格。从标志其跳出商业片一般模式、作者意识开始觉醒的《风柜来的人》开始,侯氏镜头就以精简,克制,疏离,和超过一般全景范围的“安全的”远距离而著称。他的影片中,摄影机的运动极为节制,如其代表作《悲情城市》中,绝大多数画面摄影机保持静止,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做缓慢的运动,一个场景是伴着风琴声和小孩的歌声,镜头和着音乐的节奏缓缓的摇移,由可爱的小学生摇入风琴前弹唱的静子,再摇,靠在风琴边凝视着静子的宽荣入画,这个运动长镜头使情绪得以一气呵成,只觉余韵袅袅。再如文清到山中探望宽荣,镜头缓缓地摇摄:青山绿树,水田里犁田的农人……一派田园景观如中国古典画卷轴般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这个运动长镜头的美学理念承袭了古典文学和园艺中常用的“移步换景”之法。《海上花》中大量的横移镜头亦取此法,侯孝贤对中国文化意韵的有意识的追求可见一斑。在影片中,观者常常会被摄影机从容不迫、尊重生活真实时间流程的状态所触动。那几乎静止的安放在客厅门廊外的摄影机,似乎永恒的对准了某个海上岛屿中的书寓,闲敲棋子落灯花般的讲述细腻而琐碎的情感纠葛。这是一种具有东方传统气质的电影时空,是东方电影从传统文化记忆中自然孕育的艺术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东方电影中非常重要和独特的视听传统。
中国电影的时空形态无疑是渗透着这种形式含蓄、隽永的精神。传统文化铸造了民族本土的艺术精神,使得中国文学、戏曲、舞蹈、音乐等艺术样式具有这极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和元明戏曲体现着孔儒的伦理以及社会化的亲政治性,民间舞蹈、音乐和戏剧则更是有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极度的虚拟象征性。但东方传统文化呈现出另外一种重要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对于外来艺术形式的本土化的改写,那就是对于电影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本土化消化以及对于电影时空观的东方式理解。摄影带着先天的“客观性”,“日常生活的况味”很早便被提出为电影的一个美学目标。基于“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官知觉是连续性的”这一原理,法国电影学家巴赞于经典著作《电影是什么》中褒扬长镜头的拍摄手法,以鼓励打破苏联导演艾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人倡导的把现实时空割裂,通过后期的剪接,重新组合的蒙太奇美学。但侯孝贤的长镜头美学,并非是对巴赞长镜头理论的生搬硬套,而且是结合中国电影工业的现实和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气质内涵而形成的独特镜头风格。侯孝贤电影习惯于用长镜头拍摄自然环境,远山和海滩以及自然的街景巷陌。他是尊重环境的,也是把环境当作最大的叙事对象。对于“环境”和“自然”的拍摄态度体现了侯孝贤电影美学中的“自然”观念。《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成为最终极的境界,老庄思想中的“自然”有着与宇宙秩序相关的意味。而天人合一的另一个层次,人,也是侯孝贤电影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侯孝贤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他的影片关注的是人,人的状态和人的心理。他认为镜头的画面是有两个层次,表面的,和潜流的,可能在某一个镜头中,人物并没有大段的对白或者动作,但是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表情和轻微的细节却塑造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这种将法国新浪潮式的纪实美学风格与“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经验的结合,从对单纯的渴望复制现实的影像到追求复杂的现实处境中的弦外之音,在电影语言上,侯孝贤自觉的从远镜头的客观记录转向了带有大量主观视角的侯氏长镜头美学。相比较于早期将摄影机设置在数十米外、采用望远镜头远距离拍摄带来的冷漠和疏离的感觉,愈加成熟的侯氏长镜头风格里更多的融入了中景和近景在同一镜头里的游移和转换,使得影像有了更加亲切的情感,也使得观影者在情感上获得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自然体验。《海上花》是侯孝贤镜头数目最少的电影,总共才37个镜头。长镜头风格造就了极少的镜头量,和单镜头内对于具有蒙太奇原则和功能的场面调度的讲究。长镜头更体现了作者对环境空间的极度尊重,和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表现。长镜头把对于演员的镜头表演转化为类似融入影像空间的日常生活场景。更重要的是,这种长镜头美学,最大程度的发掘画面内所蕴含的信息的容量和流动性。在这种镜头美学转变的影像下,从1993年的《戏梦人生》开始,侯孝贤的影片剪辑从“气韵剪接法”转化为“云块剪接法”。云块剪接法的特点是一大块一大块完整段落的剪辑,像云块一般的重叠上去,从而造成质朴、客观、自然的叙事感。正是这种从大量生活的角度和客观注视环境观察方式,并在镜头的运动上精心取舍,使得侯孝贤的电影从剧本(大部分是朱天文、吴念真与其合作所撰写剧本)的写作到影像的营造乃至剪接风格都得到了强化,造就了一种尊重现实世界本真面貌、对生命状态保持恬淡冷静地观察以及从容不迫的现场感的侯孝贤式影像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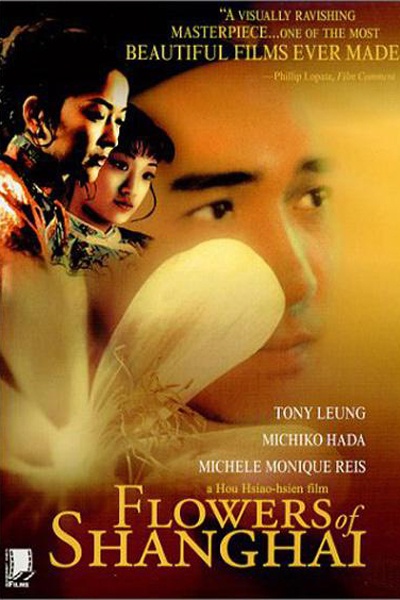 《海上花》海报
《海上花》海报
略笔也是侯孝贤镜头美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叙事笔法的省略我们也许可以从朱天文的拍片笔记分析中进一步得到解释:“侯孝贤在结构上的大胆省略,以他自己的说法是取片断,用片断呈现全部。他说:‘问题是,这个片断必须很丰厚,很饱满传神,像浸油用的绳子,虽然只取一段,但还是要整条绳子都浸透了进去。’一个片断一个镜头,连接片断之间的并非因果关系,而是潜流于镜头底下的张力、弥漫于画面之中的气息。连带在他影片中一向特有的节约,更节约了。他善于借存在于镜框之外的空间、声音、时间,以虚作实,留白给观众。由于省略和节约,剪接上他常把尚未发生的事先述了,不给一点解释或线索,待稍后明白,始追于前面片段的意义。观者得一路回溯、翻耕,不停地与整个影片经验对话----所以单一镜头里,可能疏忽已十年。”当《海上花》的开篇音乐幽幽响起的时候,观众就仿佛在徐徐展开一幅长卷轴的丹青山水画,渐渐流淌的时间,和慢慢呈现的空间在舒展的动作里平行而生动的呈现。这样长卷轴画卷,欣赏它的过程,就在于徐徐展开的过程,逐渐铺展和互相补充呼应的时空中间是宣纸的留白或镜头间的明暗交叠。长卷轴国画是东方时空特征最为准确的一种表达,而画上的景致虽然有民居或是山林的阻挡,却是层层推进的一览无余。它是大广角立体囊括众生的而非平面印刻的,它是层次丰厚,而非聚焦于一点的,它是历时的而非共时的。它是东方美学的集中表达。对于这种非戏剧化的时空,在风格上和侯孝贤有着相近美学特征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朗曾经这样阐释:“用情感表现一出戏很容易,或者是哭或者是笑,这样就能把悲伤的心情获悉月的心情传达给观众。不过,这仅仅是个说明,不管怎样诉诸情感,恐怕还不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风格。抽掉一切戏剧性的东西,不叫剧中人哭泣,却能表达出悲伤的心情,不描写戏剧性的起伏,却能使人认识人生。”
在空间处理上,侯孝贤也有着省略和写意的原则。起居室和餐厅是人物活动比较集中的内景空间,也是侯孝贤电影最经常取用的内景空间,而绝少有剧场,公司办公室,大型商场这类的公共空间。这种起居室模式的叙事空间场景,仿佛在一个家庭之内,在每天固定的家人齐聚的时刻,所有的问题,包括情感关系和矛盾都能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得以呈现。学者何乃英在《东方文学概论》中指出东方古典文化(特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特点时,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写意手法和中和之美”。他认为写意手法是关乎抒情技巧的,而中和之美是关乎精神内容的。写意手法和中和之美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心理,空灵而非真实,神似而非形似,成为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的美学特征。《海上花》亦是彰显了写意的美学思想,成就了这种对于公众来说属于私空间,但是对家庭成员来说属于公共空间的起居室内景影片。尽管《海上花》因为预算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办法实地或是搭景塑造19世纪末上海石库门里弄的街景,而全部在室内取景,是这部华美影片的一大遗憾。但侯孝贤在影像上,擅于利用人造光源和自然光源互补、利用布景制造色彩视差形成空间纵深感、充分利用空间内部的光影分割层次等技术手法,使封闭型空间延伸出来向开放型的画外空间转化,所以并没有造成取景空间束缚剧情和人物的塑造。而时光的刻意断流,戏剧性情节的刻意舍弃,和空间的刻意集中与分割,就仿佛古典的泼墨写意画,淡淡的墨迹仿佛暗示着远山上的炊烟,但又无法确定那或许只是一块云朵。片中一个倌人含怨弹起琵琶,转而又在自己的绣床上端坐带笑凝望对面榻上吞着鸦片烟的男子,被省略的空间里,究竟是金钱夺了美人的泪眼,还是巧语赚得了香腮上的笑颜,观众只能在这写意的片断里如痴如醉的暗自期许和小心揣度。
自然,省略,写意,这便是以《海上花》为代表的成熟期侯孝贤气韵镜头美学的要义。
二 《海上花》中的镜头内部蒙太奇
长镜头派和蒙太奇派是世界电影理论史上两大著名的学派。经典的长镜头理论认为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能够完成表达一个独立意思的任务。长镜头通常要符合镜头时间长,景深大的特点。而从广义的蒙太奇定义上来说,爱森斯坦概括出了蒙太奇的表意功能:即组合。他说:两个镜头并列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一个新的创造。他认为,“摄影机拍下的未经剪辑的片断既无意义,也无美学价值,只有按照蒙太奇原则组合起来之后,才能将富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视觉形象传达给观众。单个镜头也可以是蒙太奇整体。”这样,蒙太奇被引申成了一种组合和选取的原则。基于这个引申原则,在电影制作中,首先需要按照剧本的要求,分别拍成许多镜头,然后,再按照剧本的艺术构思,把这些镜头有机地、艺术地加以组织剪辑,使之产生连贯、呼应、对比、暗示、联想、衬托、悬念及形成特定的节奏,从而组合成各个有组织的片断、场面,直到成为一部为广大观众理解、表达一定思想内容的影片。然后,又按照剧本的艺术构思,为这部影片配上音乐。这种声音的构成,是按照音响蒙太奇的组接方法,与画面组合的。此外,还有色彩蒙太奇等等。那么,这些蒙太奇元素都可以称为外部蒙太奇,它们是作用于单个镜头外部的蒙太奇元素。而在镜头内部,电影导演通过场面调度,在一个不间断的镜头拍摄过程中按照蒙太奇的组合原则,用摄影机和人物的移动改变画面的构图,转化电影作者在画面中强调的核心信息,对进入摄影机镜框的画面进行了剪辑和整合。因此,尽管长镜头在物质形态上是一个连续的未经分割重组的完整镜头,从影视语言的叙事观念上说,它也是经过一定原则和逻辑进行选取进而组合排列而成的。
 《海上花》剧照
《海上花》剧照
在这个意义上,将具有特定功能的场面调度作为镜头内部的蒙太奇就是成立的,只不过它更含蓄,在手段上更加策略,是蒙太奇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一个长镜头已不是蒙太奇语言中的一个镜头了,而是构成蒙太奇的一个层次。包含镜头内部蒙太奇的长镜头,再经过外部蒙太奇的组接,构成了影片。前者作为影片的母题的阐释,承担更多镜头内部的信息整合,后者作为影片结构的搭建,承担更多的叙事功能。含有镜头内部蒙太奇的长镜头不仅在连续的时空中营造一种更加真实的感觉,而且可以通过摄影机的运动和焦点光影的变化,像分切镜头的外部蒙太奇那样,可以灵活丰实地运用蒙太奇语言实现更为复杂的表意和叙事。
在长镜头作为一种呼应、对比或回答时,往往是一个镜头与前面的一组镜头段落发生关系。这时候的单个镜头比一般的单个镜头来说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基质,而且镜头意义的含量也相对的大。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可以独立表意或叙事。它的意义的准确与完整的表达还是依靠与它发生关系的一组镜头的联系中才实现。但是即使在不能单独构成独立叙事或者表意的镜头的内部也不容置疑的存在着视觉思维,巴赞倡导长镜头要通过合理的场面调度,用不间断的镜头记录人和事物在一段时间内的运动状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遵守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完整性和真实性。但是长镜头的统一时空不是经过特技的设计等镜头切割重新组合来完成的,而是在镜头内部的运动中完成的,这与镜头组接在表达意思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镜头内部的蒙太奇与镜头组接形成的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在时空结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镜头内部的蒙太奇具有影视时空与实际时空的一致性,而镜头间的蒙太奇所创造的艺术时空与实际时空往往是不一致的。借助于摄像机和摄影机的光学镜头的景深和焦距的变化,电影作者可以在时空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实现知觉中心的运动变化。利用机位的变化来跟踪被表现的对象,保证被摄对象处于画面视觉的核心点而使前景和背景不断发生变化,是保留纪实时空感和画面内容有机阐释母题的一种结合。
下面,仅以《海上花》中第一个和第二个镜头为例,具体分析影片中侯孝贤的镜头内部蒙太奇的应用。
 《海上花》剧照
《海上花》剧照
第一个镜头就气势极大,长达近9分钟。由于在租界狎妓不受管制,大小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游戏风月场的好戏便连台上演,在书寓放酒请客称为“做花头”,电影就在“做花头”中开场。 这样的场面很像今日普通餐馆里司空见惯的景象,喧闹、热烈,划拳行酒令,加上各种风月场上的小道消息从这里不胫而走。作为开篇第一个镜头,导演借此交待了背景,勾勒出了影片的一个大概风貌:不停息的日日笙歌里,总有人欢喜,也总有黯然神伤,此时满怀心事的就是王莲生王老爷。这场戏不仅生动的写出了王老爷内心的忧伤,洪老爷的场面练达,周双珠的大气周到,更是一开场就为全片最大的情节主线埋下伏笔——王莲生与两个官人的情感纠葛。在酒席正酣之时,王莲生与周双珠耳语一阵旋即离去。众人的笑谈中讲出,王莲生常与沈小红来往,后来又去了张惠贞处,这打翻了小红的醋坛子,便要对惠贞大打出手。几个倌人和客人就此议论开来,各自辩护,一个倌人的打趣道:“哎呦,做你一个人的,不敲你,敲谁呀,大家说对吗?”,众人笑开,继续划拳,画面渐暗镜头结束。
这个镜头流畅而一气呵成,餐桌边二十几人或站或坐,不仅面目全部交待清楚,而且有详有略,氛围热烈,同时细节丰富。9分钟的时长内,镜头运动的方式基本是固定机位的左右平摇,辅以个别为了照顾人物调度站起坐下的上下摇镜, 以及个别为了配合景深的摄影机轻微的前后移动。镜头的左右摇移缓缓而规律,仿佛已经有了钟摆一般的节奏感,随着餐桌左右两边客人的发言笑谈而更替。比侯孝贤早中期喜用的远景镜头更近的拍摄距离,和自然应激反应般的延迟摆动,常常造成画面内共时性的画外音。仿佛是同坐在餐桌旁边的一位看客, 因为两边客人精彩发言而应接不暇般,简单的摇镜头又有了一丝主观性质的关注和热情的效果。镜头不断运动,焦点也在不断调整,深浅景深的变化与镜头的横向移动结合在一起,同时,镜框内的画面构图利用了布景和灯光的剪裁成了不同区块,使得不在画面核心位置的人物都得以被强调。整个镜头虽然连续但又独立成章,一个个人物的连续掠过仿佛有了正反打的叙事蒙太奇组接的效果。
 侯孝贤
侯孝贤
灯光采用的是写意的布光方式,画面内的光亮完全来自于餐桌上煤气灯的照明,两个光源在空间上纵深排列,塑造了低反差的软光效果,灯光的质感柔和,阴影的区域也相当有透明感。另外,为了弥补广角镜头和狭小空间的弊端,加强在镜头空间内纵深和通透的感觉,在画面的最远处,也布有一盏非照明用的光源,使餐厅的外间明亮可见。这样就由近及远的在空间上形成了暗——明——暗——明交替的几个过渡带,使景深镜头里的空间层次更加丰富和拉伸。色温低至1800K左右的煤气灯与烛光,为整个画面营造出高饱和度的暖色调,而闪烁的光源反射在人物服装上轻柔光滑的丝绸布料和餐桌上光泽剔透的瓷器上,造出多个高光的闪点摇曳其中,配合画面内容上的猜拳酒令,营造出一片香软微醺的氛围。
(三)蒙太奇元素在场面调度中的体现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通过场面调度手段实现的镜头内部蒙太奇,同样具备外部蒙太奇在叙事和营造氛围上的功能。在类型片中,常常出现的蒙太奇手法有交叉蒙太奇,重复蒙太奇,心理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对比蒙太奇等等。《海上花》中的镜头内部蒙太奇也相对应的体现了这些外部蒙太奇元素,而且内部蒙太奇与外部蒙太奇的交互使用,也提高了影像的表现力。
1,重复蒙太奇。重复蒙太奇是一种比较基本的表现蒙太奇手法,它相当于文学中的复叙方式或重复手法,在这种蒙太奇结构中,具有一定寓意的镜头在关键时刻反复出现,以达到刻画人物, 深化主题的目的。《海上花》中,镜头内部的重复蒙太奇结构是通过同一镜头内部循环的重复构图,类似重复蒙太奇,表现双重锁闭的“岛屿”母题的。例如:第4个镜头和第33个镜头中,周双珠处与洪老爷的两场。周双珠的大气从容已经颇类正房,洪老爷对其的器重信赖也非一般客倌所及。这两个镜头反复出现周双珠侧坐桌边一边同洪老爷交谈一边抽烟的构图,主光源在画面右侧黄金分割处,使得周双珠的脸成为画面中最亮的区域,并且由于距离光源较近,脸上形成了较浓重的侧影,是软光源营造出的侧硬光。周双珠几次同洪老爷谈起关于双玉,双宝,手中的烟火纸忽明忽暗,半变脸光亮严肃半变脸柔和阴暗,而神情话语却似外人冷眼旁观,点评“幺二”长短的味道,这是对岛屿外人看岛屿内人的观点的传达,而这种“跳脱”出来居高临下的清醒的点评,却恰恰来自于一个位于岛屿中心的岛内人,更加显出了岛屿的界定的森严。
2,交叉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的特征在于,它所表现的是同一时间内的两条或多条线索的齐头并进,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彼此依存,互相促进,而且发展迅速,交替频繁,最终汇合在一起。在侯孝贤处理的长镜头中,内部的交叉蒙太奇结构表现为镜头的缓慢水平摇移而形成的空间连续感的间断。镜头在同一场景的两组人物之间摆动,因为中间其他景物的插入和过度,穿越了画面中明暗或者色差的界限,反而造成了同一时空感的削弱,形成了互相呼应的并行发展线索。例如第二个镜头中,沈小红,丫鬟和姨娘,王莲生和洪老爷这些角色因为场面调度的分配,被明确的分成了三组,镜头在这三组之间的游移,在演员之间的布景之间时速度毫无变化,形成了空景打破叙事的效果,反而呈现了相当于三组平行交叉画面蒙太奇的组接效果。
3,心理蒙太奇。这是人物心理描写的重要手段。它通过镜头的组接或声画的有机结合,生动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比如梦境、回忆、闪念、幻觉、遐想等,其特征是声画形象的片断性、叙述的不连续性、节奏的跳跃性,故而在剪接上多用并列、交叉、穿插的手法,声画形象的主观色彩非常浓郁。现代电影中都比较广泛地运用这一手法。在《海上花》中,心理蒙太奇也在镜头外部和镜头内部有机结合的呈现。第十个镜头只有15秒,与其他镜头相比非常短小,同时也是全片仅有一个全部特写镜头——一支茶几上的玉簪。这支玉簪最早出现在第九个镜头中, 王莲生的新欢张惠珍请洪老爷替她置办这些头面,又连续出现在了第十一个镜头中,沈小红也买了同样一直玉簪在手里把玩。而贯穿第九,十,十一这三个镜头的是王莲生的一段画外音独白:“我刚认识她时,她跟我讲、做倌人最难的就是遇到个好客人。现在遇到我,在有新客人也不做了。我讲你不做就嫁给我。她口口声声说好。其实都是在敷衍我,当初说还债就嫁,还了债又说爹娘不许。我当她是不想嫁人的。不知她心里是怎样想的。”可以说,这只玉簪就像王莲生对这两个女人的意义,对张惠珍,王莲生是她不愿还价也要买到的挚爱,而对沈小红,王莲生则是她糟踏十块钱也不愿意别人独有的赌气之物。这样的剧情下,第十个镜头具备了内部,外部两层蒙太奇的意义。作为单独的镜头,对这个玉簪的特写宛若是王莲生的主观镜头,凝视着这只玉簪出神,烛火斜照在茶几上,玉簪虽然剔透,但是光亮却也摇曳,也许他亦在思考自己对这两个倌人的感情。而作为连接前后两个镜头的组接,这个特写镜头又承担了叙事和表现的外部蒙太奇功能。
 侯孝贤
侯孝贤
4,对比蒙太奇。对比蒙太奇是极富有镜头表现力和暗示力的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或场面、段落)之间在内容上(如贫与富、苦与乐、生与死、高尚与卑下等)或形式上(如景别的大小、色彩的冷暖和浓淡、光线的明暗、声音的强弱、动与静)的强烈对比,产生相互强调、相互冲突的作用,以凸现创作者的某种寓意或强化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侯孝贤非常善于利用光影和布景的变化来营造对比蒙太奇的效果,例如在第七个镜头中,倌人黄翠凤先是在里间同客人罗老爷谈话收拾装扮,此时光影全为暖色柔光,然后另一个倌人珠凤跑来哭诉,被黄翠凤痛骂一顿,此时在楼梯外间布置了一道非常硬的底光,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形成了非常浓重的强对比阴影,突出了黄翠凤寓所大量西洋风格铸铁装饰的冷硬,两相对比,黄翠凤泼辣精明,强悍的性格一下子被凸现出来。
在镜头语言上,侯孝贤在《海上花》中一反常态,完全摒弃了远景的使用,转为用亲密的近景大景深长镜头将电影空间收进内室中来。《海上花》中,侯孝贤似乎走到了一个美学的终端,全篇不到40个的镜头,竟不及好莱坞一般商业制作影片流行镜头数的1/50,全部的方言对白和室内自然光源照明,这些都是现代电影工业中反常规的现象。然而,无论是故事主题的细腻幽深,还是场面调度的华美精巧,甚至仅仅是如同手工艺品一般精湛的画面质感,都彰显着是一种风格上的超越。从《风柜来的人》到《海上花》,侯孝贤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从前以为镜头必须拉远一点,才能展现出一种俯视的、不带情绪的观照,到了《海上花》我发现其实不然,这种视角取决于你如何呈现剧中人,如果你自己在现场是非常冷静的、冷酷的,你喜欢他们、热爱他们,可以和他们一起。但又有一双眼睛在一旁看着他们,即使镜头再近还是可以有那种效果。摄影机就像人在旁边,这个人就在旁边,他在旁边看看这一群人,有时候在这边看看这个人,然后那边有声音他才回过头去看,摄影机不可能像镜头转得那么快,它就可以慢慢的转过去,可能转过去时那个人又已经走掉或不讲话了,都无所谓。”
每一场戏,每段关系,都在黑暗的狭窄的场景中慢慢亮起拉近,再在逐渐暗淡的光影中慢慢远离。小小的戏场,短暂的演出。烟花女子的故事或许承载不起沉重的历史和意义,却在看似轻淡的一段段景中将复杂的情感,不安定的人生水墨画卷般徐徐展开。虽然电影《海上花》更像是窥取了这些百年前的海上之花的零落的生活片段,但是乱世中短暂的安逸,风尘中别样的花样年华更让人叹息。而这部影片本身,也像是一朵精致的奇葩,不仅有着华丽令人惊叹的容颜,也有着耐人寻味的内涵。 作为侯孝贤的第十部长片,《海上花》呈现的不仅是海上倌人让人心痛,让人着迷的凄然之美, 更体现了一个成熟导演在镜头美学上纯熟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