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卢瓦百年诞辰。在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意义最深远的一项便是《朗格卢瓦:电影书写》的出版。朗格卢瓦的这本文集由两位法国电影学者不惜花费数十年时间搜集整理而成,从中不难窥见朗格卢瓦对于电影的狂热的爱。本刊特约撰稿人于近期对他们进行了专访。本刊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最伟大的影迷的纪念。
 亨利·朗格卢瓦
亨利·朗格卢瓦有太多头衔可以安在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1914 年 11 月 13 日-1977 年 1 月 13 日)身上:电影保护的先行者、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新浪潮”教父。他本人最为认可的头衔,或许还是——一个影迷。在朗格卢瓦生前,他就是影迷们的精神领袖, 1968 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André Malraux)罢免他的馆长一职,导致特吕弗(Franois Truffaut)、戈达尔(Jean-Luc Godard)、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等导演走上街头抗议并和警察发生冲突而酿成“朗格卢瓦事件”便是最好的证明。即便在他百年诞辰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影迷。
 在历经十数年的搜集整理工作之后,厚达 800 页的朗格卢瓦文集《朗格卢瓦:电影书写》于今年出版,无疑这是他百年诞辰的最好献礼
在历经十数年的搜集整理工作之后,厚达 800 页的朗格卢瓦文集《朗格卢瓦:电影书写》于今年出版,无疑这是他百年诞辰的最好献礼为了纪念朗格卢瓦的百年诞辰,今年法国电影资料馆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大型电影回顾展、以朗格卢瓦电影博物馆为主题的展览,以及同戛纳电影节合作拍摄的十三部当代电影人追缅朗格卢瓦的短片。在历经十数年的搜集整理工作之后,厚达 800 页的《朗格卢瓦:电影书写》(Henri Langlois:Ecrits de cinéma)也同期问世。这本文集由影评人、电影资料馆文化处负责人贝尔纳·贝诺列尔(Bernard Benoliel)和电影史学家贝尔纳·艾森希茨(Bernard Eisenschitz )编辑整理。相信通过这两位电影专家的对谈,可以更好地了解朗格卢瓦这位电影史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一个没有拍摄电影却“导演”了电影的痴狂影迷,一个从零开始徒手创造了“电影卢浮宫”的天才。
B=《外滩画报》
B.B=贝尔纳·贝诺列尔
B.E=贝尔纳·艾森希茨
一个并不出色的诗人的诗意写作
B:这本文集的编辑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已有珠玉在前:1986 年前,资料馆曾与《电影手册》合作推出过一本朗格卢瓦的文集。但是现今的这一本增添了非常多的内容,尤其是他年轻时期的日记。
B.E:这本书的结构经历了几次变化,十几年前资料馆就有了将其保存的朗格卢瓦手写日记整理出版的计划,继而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并不是关于电影,而是他青少年时期的感触、与家庭关系的记录,甚或是他尝试写的小说。这些与电影并不相关的内容我们都没有编入。整理过程结束,我们发现这些年轻时期的日记并不适合单独成书,因为它们只牵涉到很短的一个时期(1931 年-1939 年)。于是我们抱着最大化的想法将其扩充成一本近乎全集的文集,一些在上一本书出现的内容我们再次将其编入,当然我们也舍弃了另一些。
B.B:在资料馆保存的大量手写日记中,我们也编入了他类乎自传的文字,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年轻时代的朗格卢瓦;更多的则是他那个时期关于电影的书写,观影的感想、电影评论的自我锻炼,以及如何通过书写培养自己对电影的认识等等。由这些内容组成的全书的第一部分几乎都从未出版过;接下来的部分则是他在不同地方发表的文章、序言,或者是资料馆放映计划上的专题文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很多被人完全遗忘的内容,其中也有很多我们很幸运地就无意中遇到了。
 朗格卢瓦弟弟乔治和美国学者格伦·梅伦特共同撰写 亨利·朗格卢瓦的传记
朗格卢瓦弟弟乔治和美国学者格伦·梅伦特共同撰写 亨利·朗格卢瓦的传记B:这些朗格卢瓦年轻时期有关电影的日记曾经在由朗格卢瓦弟弟乔治(Georges P. Langlois)和美国学者格伦·梅伦特(Glenn Myrent)共同撰写的传记中片段式地出现了一部分。当我在这本书中读到更多的时候,深深地被震撼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并不比电影年轻多少的人,在那么年少时就对前者充满了热情,更重要的是非常坚定的信任,对电影未来的信任和电影本身的信任。他青少年时期的日记大部分都编入此书了吗?
B.E:在他的日记中也写了一些现在被人们彻彻底底遗忘了的电影,有一些这样的文字出于篇幅上的限制我们也没有录入。更重要的原则是,我们选择了那些可以表现出其电影批评意识养成的书写。
B.B:电影批评意识的诞生。
B.E:曾经阅读过这些内容的人有很多非常喜欢他那一时期写的电影评论,他们认定在那个时期朗格卢瓦就已经成了最好的电影评论家之一。我觉得这么说也可以,但是这也归功于我们并没有将所有的内容编入。(笑)
B.B:是的,我们选择了其中最好的内容。其实资料馆保存的朗格卢瓦档案中还有一些是他学生时期的作文,或者是自己写的时评、政治观点,没什么进展的剧本,有些甚至是他为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国家做出的规划,这些在我们看来无法历久弥新的内容我们都没有采入。但是这四十本日记都由资料馆妥善保存着,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阅读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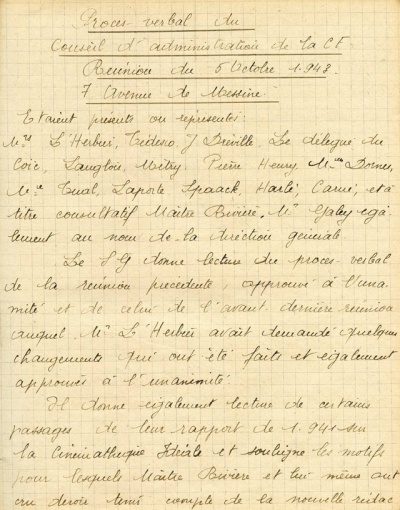 朗格卢瓦的日记由法国电影资料馆妥善保存着,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阅读
朗格卢瓦的日记由法国电影资料馆妥善保存着,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阅读B:书中有很多有益的注释,其中我们可以探寻到朗格卢瓦某些想法的源头,比如他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保存一切,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没有任何一个电影资料馆拥有这个理念。它的诞生则是来自于观看路易斯·菲拉德(Louis Feuillade)《方托马斯》(Fantmas)的经历: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蹩脚的电影,但是朗格卢瓦却非常喜欢……
B.B:那些对某些人毫无意义的电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是如获至宝。因此他说只需要让时间来做出筛选,但是如果我们不保存一切,那么就无法做出筛选。
B:关于朗格卢瓦的写作方式,或者说他的文笔:他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影评人,而当我们读他文章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口语般的流畅感,仿佛是听一个关于电影的演讲。
B.E:的确,我感觉这是他流畅的思考在文字上的展现。他不需要预先做出提纲就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而他的博学则为这一点提供了保证,当我们在整理他的文字的时候,很明显地能感到他不是那种写写停停,查查资料的人。而这种口语化的表达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并不出色的诗人的诗意写作,因为当我们阅读他的诗作的时候,觉得他作为诗人并无才华;但阅读他其他的文字,却觉得有些诗意,有的时候还朗朗上口。
“无序”的管理者
B:可以描述一下现实生活中的朗格卢瓦是怎么样的吗?
B.E:我曾经和他共事过一段时间。认识他是更早的事,从我经常去资料馆开始。1969 年或者 1970 年的时候,我们在莫斯科电影节遇到,在那之后不久,他就找我来负责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电影史文集的编辑整理工作,于是我同他展开了合作,或者询问他一些问题,要一些资料,总体上说我没有怎么得到答复。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滔滔不绝的独白者,你如果不懂他说的一些事情,就得马上记下来然后自己去搞明白。比如萨杜尔《电影史》的编辑工作,最开始朗格卢瓦告诉了我一些特别有启发的事情。实际上萨杜尔并没有完成《电影史》的撰写工作,但似乎也不应止于默片,朗格卢瓦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偶然,他推测到因为在那一时期萨杜尔察觉到独力完成世界电影史的撰写是不可能的;何况同时他作为电影评论家发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比如印度、古巴、拉丁美洲、埃及等等。后来无论在编辑萨杜尔的电影史著作还是电影批评文集的时候,都一再印证了朗格卢瓦的这个推测。但关于这个推测,他只告诉了我一次,之后我再去问他相关细节,他都闭口不言了。
B:基本上可以说朗格卢瓦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写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是让人震惊,没想到他写了这么多!
B.B: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打破一个悖论:一个主持了电影资料馆四十年、终其一生没有停止书写的人竟然在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书!同时有另一个想法,和刚才艾森希茨说的萨杜尔很相像的是,朗格卢瓦同前者一样,他们的视野是世界性的,并不是停留在某一国别的电影或者某一类型的电影。在整理他的文集的时候,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他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电影计划。同时这也是他作为策展人一生中都在做的事情,展现电影世界,展现世界电影。
B:比如说他最早且不断地在资料馆放映小津安二郎的作品直到这位日本电影大师赢得他该有的声誉,比如他对伯格曼(Ingmar Bergman)、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电影的发掘,更不用说那么多曾经被人遗忘的大师在资料馆重新找到荣耀。
B.B:这也是朗格卢瓦的伟大之处,不局限于某一国的电影,着眼于电影的世界。
B:说到电影资料馆和萨杜尔,我发现其实萨杜尔在电影资料馆甫一建立(1936 年 9 月)就在报纸上撰文书写这件事,也就是说他预见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艾森希茨先生,作为萨杜尔专家,我想请您说一下朗格卢瓦和萨杜尔的关系,我们知道,除了亲密无间的信任和友谊之外,他们也有关系很紧张的时期。
B.E:一方面说来,朗格卢瓦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二战后,和抵抗运动相关的电影文化运动兴起,主要是各种电影俱乐部的创建,朗格卢瓦有点把他们视作自己的竞争者。
B:而萨杜尔正是电影俱乐部联盟的秘书长。
B.E:还有一点,内有法国共产党遇挫,外有冷战大局势,而萨杜尔正是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再次真正地“相遇”应该是“新浪潮”的时候,“新浪潮”是对“电影是什么的”这个问题的总结性回答,而这也恰好验证了他们两人的电影观。萨杜尔在那个时期文笔更胜一筹,在研究电影史的同时对新电影的评价也非常敏锐;朗格卢瓦在那时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因为很大一部分“新浪潮”的弄潮儿都自称是在资料馆学习了电影,是“电影资料馆的孩子”,这是其他任何一个电影流派都没有的情况。
 1968 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罢免了朗格卢瓦电影资料馆馆长一职,夏布洛尔(中间举牌者)、让·鲁什(中左)、戈达尔(中右)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1968 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罢免了朗格卢瓦电影资料馆馆长一职,夏布洛尔(中间举牌者)、让·鲁什(中左)、戈达尔(中右)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B:一直到 1968 年的“朗格卢瓦事件”,当国家想“解雇”他时,以“新浪潮”导演为首,大家捍卫了他的电影资料馆。
B.B:关于朗格卢瓦和萨杜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朗格卢瓦向萨杜尔开放了自己的电影收藏,这对于后者书写自己的电影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也向萨杜尔提供了 1943 年自己组织的电影历史研究会的所有资料。1943 年的时候,电影评论远没有之后成熟,电影史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朗格卢瓦当年搜集、采访而汇聚成的史料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不可或缺。
B:而萨杜尔也对资料馆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比如他捐给资料馆大量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我记得朗格卢瓦说过,萨杜尔去世之后,他感觉资料馆仿佛都不复存在了。那么萨杜尔曾经对朗格卢瓦管理下的资料馆的“混乱”情况非常不满吗?
B.E:混乱可是不加引号的,所有人都知道。这种管理上的问题,不仅对于电影资料馆这样的新生事物来说会出现,有的时候甚至国家也会犯错误。对于资料馆来说,朗格卢瓦身兼两个职责,一方面就是电影资料馆或者电影博物馆的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对前者的管理。管理这个工作对于朗格卢瓦这样性格的人来说太难了。而且在生命的后期,他需要不断寻求资金上的援助,见不同的人以便能得到一些赞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别人,这些不必要的精力付出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负担。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的双重职责附加到一个人身上,我从来也没见到任何另一人可以做到更好,至少我认识的人中没有。朗格卢瓦缺乏管理的才能,他身边的团队也是为了那个更伟大的职责而产生并运作的,并没有多少人擅长管理这件事。总体上来说,大家对资料馆管理混乱的抱怨不是无缘无故的,或者对朗格卢瓦有时候不按常规做事情也颇有微词,但我的确没有见到谁能把这两件事都做得非常出色。
B.B:也许可以说朗格卢瓦的性格造就了资料馆的混乱,但我觉得有一点也必须得说,那就是从 1936 年资料馆创建到 1959 年马尔罗担任文化部长,资料馆基本没得到国家的补助,管理一个存有上万部电影的资料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反过来说,有二十年的时间,资料馆奇迹般地依靠近乎志愿工作的人一直在放映电影。因此我们不可以简单地重复说朗格卢瓦的“无序”。
B.E:我们可以。(笑)
B.B: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地说明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他近乎以一已之力完成这样的工作。说起混乱,让我想起一件趣事,1950 年代初萨杜尔在索邦大学任教,那时他经常在课上播放电影片段,当我们在整理朗格卢瓦的书信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他写给朗格卢瓦的信,内容大概就是“如果电影持续地不能准时到来,我这个关于喜剧或者滑稽电影的课程就真的要以悲剧收场了”之类的。我们感受不到在那时放映一部电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在当下,想看一部电影是何等容易。
 1974 年 4 月 2 日,朗格卢瓦从演员金·凯利和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手中接过奥斯卡荣誉奖
1974 年 4 月 2 日,朗格卢瓦从演员金·凯利和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手中接过奥斯卡荣誉奖藏在放映机中的导演
B:回到朗格卢瓦的人生,“新浪潮”的诞生和“朗格卢瓦事件”可能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世人也往往顺水推舟,因此经常会有“是朗格卢瓦催生了新浪潮”之类的说法。
B.B:关于“新浪潮”的诞生,朗格卢瓦和巴赞(André Bazin)等人确实为他们这一批新导演准备好了物质条件。有意思的是,那时的特吕弗、戈达尔(Jean-Luc Godard)、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等人其实只对朗格卢瓦的一面感兴趣并着迷,那就是“策展者朗格卢瓦”,他们需要且只需要朗格卢瓦给他们放映电影。而对资料馆的主人来说,还有另一件事与放映电影同样重要,那就是“展览电影”。电影博物馆或者其他关于电影的展览,“新浪潮”导演们丝毫不感兴趣。特吕弗是“朗格卢瓦事件”里毫无疑问的核心人物,但在之后他也不解为什么自己曾经捍卫过的人转向了电影博物馆,怎么走向了“歧路”。这是一个他们不太感兴趣的朗格卢瓦,他们也不明白后者这样做的原因以及这样做的重要性,他们只需要看电影而已。
B.E:但是资料馆的最终极任务还是要在放映厅中完成的,别忘了,即使是展览,目的还是吸引人们步入影厅,而不是相反。因此对于“新浪潮”来说,他们所认识的电影首先是大量在影厅中放映的电影,这很正常。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在序言中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还是电影学院学生的时候,学校里经常让他们分析一些他们从没看过的电影;当我六十年代初在资料馆看电影的时候,也经常听到一些笑话,比如一些历史学家会郑重其事地写他们从没看过的电影或者是也许四十年前看过却从未再看的电影。因此重要的是看并且大量地看电影,判断并重新判断看过的电影,从这一点讲,“新浪潮”这些人只对朗格卢瓦的某一面感兴趣也属正常。
 特吕弗(右一)是“朗格卢瓦事件”里的核心人物,但之后他也不解为什么朗格卢瓦(右二)转向了电影博物馆
特吕弗(右一)是“朗格卢瓦事件”里的核心人物,但之后他也不解为什么朗格卢瓦(右二)转向了电影博物馆B:朗格卢瓦把电影看得比政治甚至生活更重要吗?
B.B:对于电影是否高于生活这个问题,这是百分之百的,就像特吕弗一样。从这点上说,电影压倒了一切,通过电影生活,借助电影进入生活。戈达尔曾经说过,朗格卢瓦其实是一个导演,但却是一个藏在放映机中的导演。他放映电影,却希望看电影的人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感到满意。这种对放映的执迷,使得即使在某一时刻他已没有时间去看自己放映的电影这件事也变得不重要。电影被人看到,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B:也正是出于此,使得他也不惮于放映一些纳粹电影?
B.E:是的,他还会经常放映自己讨厌的电影,这是他的放映策略。有意思的是,当我在读他年轻时代日记的时候,发现他非常早就表达出对纳粹的厌恶,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厌恶,我觉得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有这样敏锐的观察力还是很惊人的。战后,虽然他经常放那些反潮流甚至引发丑闻的电影,但我印象中他没有放过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或者威特·哈兰(Veit Harlan)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很谨慎的。而在一些德国电影的回顾展中,他也会放一些纳粹德国制作的电影,政治电影、娱乐电影都有,因为置于某一个环节之中的这些电影,其电影性会压过它们的政治性。
B:我对于二战法国被占时期的朗格卢瓦特别感兴趣,因为在那一时期资料馆取得了与时势稍有些不相符的发展:他与德国占领者中负责电影管理的人的良好关系(当然他们在战前一同作为各国资料馆的代表就已相识),或者与维希政府的互动,使得他一方面保护了电影资料馆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帮助了他的许多忠实合作者,比如洛特·埃斯内(Lotte H.Eisner)。
B.E:关于那个时期的朗格卢瓦,我认为是无可指责的。他从未在任何角度表达过对纳粹或者维希政府的支持。但他的确同这些人一同工作——为了保护电影,一个把保护电影或者保护其他东西作为生命的人都会像他这么做。他也确实通过这些工作保存了许多电影,也帮助了朋友。据我所知,在那个时期,他从没有因为一个朋友是犹太人而对其敬而远之,相反的例子在当时的法国电影界可是屡见不鲜。可能的妥协也只是存在于必要的、工作上的;而不合作或转入地下,对于资料馆来说,后果就是彻底被摧毁。
B.B:对于朗格卢瓦那一时期的拷问,多是苛责他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典型意义上的“抵抗者”。从这一点上说,是的,他没有加入游击队,但是他收藏的电影都成了游击队,这是肯定的。用一个众所周知的朗格卢瓦的故事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常说自己二十岁前常做一个梦,就是城市突遭大火,火光冲天,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他却到处搜集城市里的各式珍宝,将它们装车送至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将这个梦同 1940 年发生在法国的事情相类比以便理解当时的朗格卢瓦。
来源:外滩画报 文:王谟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