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晚,一辆侧身印有上海国际电影节标志的轿车停在衡山电影院门口。走下车的,是本届电影节“英才孵化计划”的艺术总监比利·奥古斯特。这位穿着白色细格衬衫、深色西装和米色西裤的丹麦导演,没有打伞就在细雨中走向电影院的VIP休息室。当晚,影院将放映他的代表作《善意的背叛》。
这不是比利·奥古斯特第一次与上海国际电影节结缘。2008年,他和王家卫一起,担当了金爵奖竞赛单元的评委。
 比利·奥古斯特
比利·奥古斯特开始访问前,我们把最新的《外滩画报》递给奥古斯特,却得知他已经让志愿者买了一份。虽然无法读懂中文,但他还是想看看将要采访他的这份报纸的风格。
在奥古斯特的陪同志愿者、东华大学的小黄看来,比利虽然话不多,却很幽默。前一天下午四点才到上海的奥古斯特,坦言没有受到时差影响,因为他在上海得到了“公主般”的款待。
为伯格曼拍电影
1991年,比利·奥古斯特凭借《善意的背叛》一片赢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登上了事业的顶峰。这是他第二次获得金棕榈奖。1987年,《征服者佩尔》也曾获此殊荣。
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只有六位导演曾两次赢得金棕榈,而《征服者佩尔》还包揽了当年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历史上,只有五部金棕榈获奖影片在第二年初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中折桂。在《征服者佩尔》之后,尚未有人复制这样的成功。
《征服者佩尔》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十岁出头的佩尔和年迈潦倒的父亲一起从瑞典到丹麦生活。他们在石头农场里饱受凌辱,见证了种种背叛、反抗和复仇。最终,不足十四岁的佩尔决意离开父亲,独自踏上征服内心世界的路途。《纽约时报》在将《征服者佩尔》列入电影史百佳影片名单时评论说:“这部影片用一种狄更斯的叙事方式,配上令人揪心的辅线,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梦想残酷地表现出来。”
相比《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背叛》对奥古斯特的个人意义更大。这是他和自己的偶像、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合作的产物。
伯格曼在拍摄描写自己父母的《芬尼与亚历山大》时萌生了退意。在1982年拍摄完《芬尼与亚历山大》后,伯格曼正式宣布结束四十年的导演生涯。此后,他只是从事一些电视电影的拍摄和剧本的写作。《善意的背叛》的剧本正是出自他手。
和《芬尼与亚历山大》一样,《善意的背叛》也是伯格曼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后者的故事发生时间比前者更早——伯格曼出生以前。这是一部关于伯格曼父母相识相恋过程中爱恨情仇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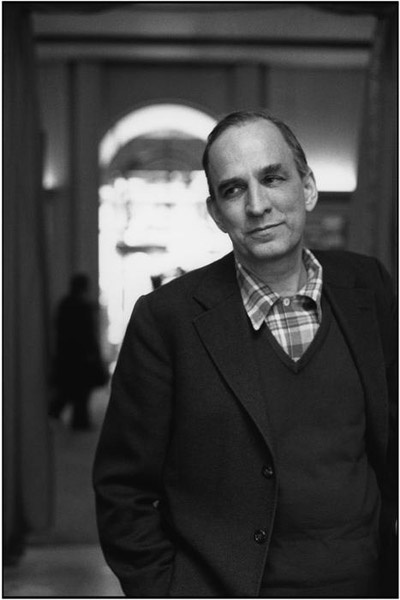 英格玛·伯格曼
英格玛·伯格曼父母对伯格曼的影响巨大。在他的自传《魔灯》中,伯格曼不厌其烦地说着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外婆。在他的许多影片中,他都以母亲作为原型进行创作。而伯格曼电影中对于宗教的探讨,又主要是受到他的牧师父亲的影响。《善意的背叛》对伯格曼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当奥古斯特受邀担当这部影片的导演时,自然是受宠若惊。
“在此之前,我和伯格曼并不相识。”奥古斯特回忆道,“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他是伯格曼,有一个剧本想让我看看,问我有没有兴趣。”于是,奥古斯特就从哥本哈根飞往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的家中。伯格曼告诉他,自己曾看过七遍《征服者佩尔》,非常赏识奥古斯特,所以才邀请他执掌此片。
此后,奥古斯特和伯格曼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每天聊四个小时。除了剧本之外,伯格曼给予奥古斯特独立的创作空间。“当然会有压力,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伯格曼的阴影之下。”奥古斯特说道,“我的压力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在如此漫长的拍摄过程中保持所有的精力。”
为了给奥古斯特减压,伯格曼甚至没有出席影片的新闻发布会。但伯格曼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佩妮拉·赫兹曼·埃里克森扮演他的母亲,担当女主角。佩妮拉曾出演过伯格曼的最后一部电影。奥古斯特重新看了一遍《芬尼与亚历山大》后,认为佩妮拉是一个合适人选,欣然接受。
就在那一年的戛纳,佩妮拉凭着《善意的背叛》中出色的表演,赢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而此时,她已经叫作佩妮拉·奥古斯特——在《善意的背叛》长达九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她与奥古斯特坠入爱河,结为伉俪。这是戛纳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一对夫妻分享两个奖项。
做导演会累,但心不累
就在当晚的奥古斯特见面会前,衡山电影院放映了本次电影节的另一位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迷》。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爱好者出于对摄影机的迷恋,成为一位获奖电影导演的故事。奥古斯特说,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善意的背叛》海报
《善意的背叛》海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送给了我一台手摇摄影机作为生日礼物。我还收到了35毫米的胶片,很短的一段,只能拍一分钟。”奥古斯特说他喜欢手摇摄影机的感觉,还有摇动时摄影机发出的声音,“我可以这样拍一整天,也不感到厌倦。”
在读中学时,奥古斯特和同学一起表演戏剧,开始写自己的故事。之后,他前往瑞典学习摄影,再回到丹麦电影学院深造。1978 年,奥古斯特拍出了他的导演处子作《蜜月》,广受好评,就此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做导演不能是冲着名气和金钱去的,那永远不会成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讲坛上,奥古斯特给出了自己对导演这一角色的定位,“演员可以休息,剧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但导演不能休息。拍完以后,你还得筹资,还得思考。”
奥古斯特承认导演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有时候会没有状态。我那时候就想自己要是个作家或画家就好了,撕掉作品了事。但导演却不能这么做。”但他坦言,做导演虽然累,但心不累。坐在剪辑室里看着自己拍的片子,是奥古斯特最享受的时刻。
奥古斯特是带有强烈北欧风格的导演。他钟情于事无巨细的史诗般叙事方式,擅于表现人与人之间残酷的关系,尤其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他认为,同伯格曼一样,自己的电影表现也受到童年成长环境的巨大影响。
比利·奥古斯特的父亲是丹麦“黑色教育法”的产物(去年上海电影节中曾展映过的一部丹麦影片《我们一定赢》就介绍了这段丹麦教育的黑暗期)。他也将这种严酷带到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来。奥古斯特回忆说,当他做错什么时,父亲总是威胁要叫“小白人”来抓他。他的童年就在对“小白人”的恐惧阴影中度过。
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奥古斯特起先也本能地无法抑制住内心的魔鬼,用恐吓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后来,他意识到有责任不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在接受了心理治疗后,他才解放了心中的恶魔:“我变得懂得倾听和理解,喜欢帮助人打开心扉。”
 拉斯·冯·提尔
拉斯·冯·提尔北欧电影的老前辈
北欧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总是有着优异的表现。在过去四年中,北欧电影曾两次在上海获奖。2007年,瑞典影片《逃往疯人院》获得评委会大奖;2009年,丹麦影片《原创人生》与《爱之伤痕》更是共同包揽了金爵奖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男女主角奖。
除了伯格曼之外,北欧国家还为影迷们贡献了诸如拉斯·冯·提尔、考里斯马基、拉瑟·霍尔斯道姆等一大批的优秀导演。近几年来,北欧电影的佳作仍然层出不穷。丹麦导演苏珊娜·比尔的《更好的世界》也像《征服者佩尔》一样,包揽了今年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
奥古斯特那一代的导演尚未完全退场,新一代的电影人却不断涌现。在电影节前,上海、北京和成都三地都举办了“瑞典电影周”的活动,八部近年来获得票房成功和影评人好评的瑞典影片呈现在了中国影迷面前。在奥古斯特看来,电影始终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电影观众大多数是年轻人。”
在世界电影版图上,北欧电影的地位虽然不算最高,但却独树一帜。老一代北欧电影冷峻、严酷,注重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诗情,被称为“灵魂的电影”。这当然和北欧国家的高纬度地理位置有关。伯格曼、奥古斯特的影片都是这一类电影的典型。
在奥古斯特之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北欧导演作品中的叙事更加直白,更好莱坞化,已经和上一辈截然不同。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北欧人冷静、内敛的天性,还融入了简约风格。如果说欧洲的电影是奢侈品,好莱坞电影是大众消费品的话,那么新一代北欧电影更像是趋于两者之间的宜家产品:大众化,又不失美感。
在大师班上,奥古斯特承认这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对《加勒比海盗》系列制片人的访谈。他们是为了MTV时代的年轻人拍这部电影的,每15分钟就会有一个小高潮。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征服者佩尔》海报
《征服者佩尔》海报“错误的是,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像《加勒比海盗》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多。真正好的电影越来越少了。”奥古斯特担心的是,属于他的时代的“严肃电影”会死去,“我想拍的严肃电影很难在美国拿到资金。电影人必须独立去做,必须跳出体制进行思考。这其实是一种悲哀。”
“但最终,选择权还是留在观众手中。”奥古斯特相信观众的鉴赏能力,“电影作为一种私人化的东西,蕴藏着一种秘密。当这种秘密和观众产生共鸣时,这一切就值了。”
那一夜在衡山电影院,奥古斯特在见面会后便匆匆离开。长达三个小时的《善意的背叛》结束时,已是午夜时分。当字幕缓缓升起,灯光亮起时,观众席里又一次爆发出了掌声。我们把这一幕告诉奥古斯特,他只是腼腆地一笑。
B=《外滩画报》
A= 比利·奥古斯特 Bille August
“伯格曼通过电影打开了一道通往人类灵魂的大门”
B:伯格曼邀请你拍摄他写的《善意的背叛》,还承诺给你独立的创作空间。
A:一直以来,我对伯格曼就充满敬仰。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拍摄一个他写的故事。我读了他的剧本,实在是太美了。所以我就从哥本哈根去斯德哥尔摩见他。他对我说,“我导演了超过50部电影,所以我知道保持导演独立性是多么重要。”
B:在接受邀请后,据说你们连续三个月每天交流四个小时。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呢?
A: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讨论剧本的细节。伯格曼是一个导演,一直以来他都是和演员一起工作,但我认为他可能没有多少和导演共事的经历。对他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原本只是计划讨论两个礼拜,但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谈论,所以延长了那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对我来说,那真的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
B:就像伯格曼的很多影片一样,《善意的背叛》中也有许多宗教元素,你们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吗?
A:伯格曼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但我们经常讨论生命与死亡的命题。对他来说,死亡只是一个从“存在”到“消亡”的过程,死亡只是死亡而已。
 《芬妮与亚历山大》海报
《芬妮与亚历山大》海报B:你认为伯格曼对北欧电影的影响是怎样的?
A: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最喜欢伯格曼的一点是,他通过电影打开了一道通往人类灵魂的大门,他把灵魂的内在用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且还非常美。但是,在新一代导演身上,这种影响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而且,必须是这样,总是得有新一代的导演冒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创作。
B:北欧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表现一直很抢眼。在过去四年中,曾经有两部北欧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获奖。在你看来,北欧电影为何如此独特?
A:在北欧国家,我们对电影制作有非常好的支持体系,政府对电影制作投入许多补贴。就拿丹麦来说,我们确实是个小国家,只有500万人口——大概只是上海人口的一小部分吧,但丹麦电影学院每年会出资拍摄30部电影。这种持续的财政补助,让很多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都冒了出来。瑞典也是一样。这种对于电影制作进行补助的传统,创造出了让导演和演员自我发挥的空间和环境。
B: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前,这里还举办了一个瑞典电影周的活动,其中大多数的展映片都是近两年的佳作。与你们这一代相比,新一代的北欧导演有什么不同吗?
A:我们这一代更倾向于史诗般的叙事方式,但新一代的导演是在 MTV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作品节奏更快。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故事。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故事,不管你拍的是MTV,还是用了3D技术,都没有用。好的故事才是电影的实质。如果你的故事本身没有吸引力,那其他什么都没有用。也许你觉得演员、剧组、剪辑、配乐可以弥补故事的缺陷。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缺陷只会越放越大。
B:如今,最引人瞩目的北欧导演就是拉斯·冯·特里尔了。你如何看待他的影片呢?
A:我没有看过太多他的影片。但因为我们都来自丹麦,所以我和他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我们是他之前的一代,在他之后又有了新一代的导演。
B:你的儿子桑德斯是一名编剧,他的作品《喝彩》曾广受好评。你会与他合作吗?
A:不会。我不想和他合作。一方面我并不喜欢他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在工作中渗入父子关系。
 《开往里斯本的列车》海报
《开往里斯本的列车》海报B:你与北欧和好莱坞的剧组演员都有过合作。你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A:没有。对于我来说,工作态度才是关键。有些演员和剧组很自恋,我不想和这些人合作。我喜欢和工作态度端正的人合作。全世界各地的剧组人员,他们都穿着相同的T恤和马甲,他们的打扮都那么相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好莱坞拍片,剧组往往有两三百人。而在北欧,我们只要有三四十人就够了。
“我不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大师”
B:当你开始正统的电影学习时,你先是去了瑞典学习摄影,再回到丹麦电影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A:最有用的东西还是手艺。我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拍摄用的工具。我学到了如何去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剧组成员合作。电影导演就像指挥家一样,要学会控制拍摄的方方面面。很多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会犯许多错误。他们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剧组工作。剧组都是等着导演来拿主意的,但年轻的导演并没有学会怎样做决定,他们会感到害怕。
B:你在1991年就第二次获得了金棕榈奖。目前来说,这是一个电影人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了。在此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挑战?
A:的确,获得金棕榈是一个专业意义上非常重要的肯定,但获奖只是获奖而已。对于我来说,最高的奖赏就是写一出好戏,再找到好的演员和剧组把它呈现出来。开动摄影机,拍出几秒钟魔法般的片段,那才是最棒的事。
B:在电影节的见面会中,你提到电影导演必须要做出妥协。但哪些东西是你不会做出妥协的?
A:虚荣。在这个行业,你会遇见很多爱慕虚荣的人。他们的自恋对电影制作是很大的伤害。个人的虚荣心会对剧组的其他成员产生消极影响。我尽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我感到很荣幸,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于我来说,能够拍电影实在是令人感到幸福的。这是我最大的兴趣,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现实生活远比拍电影更艰难。
B: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停止拍电影?
A:从来没有过。上个月,我在葡萄牙准备我的另一部新片《开往里斯本的夜车》。我遇到了一个102岁的导演,他还在工作。
 《玛丽的激情》海报
《玛丽的激情》海报B:在今年电影节“向大师致敬”环节中,展映了基耶斯洛夫斯基、郑君里以及你的作品。对你来说,谁是电影大师呢?
A:我年轻的时候,心中有很多英雄和大师,但现在没有了。我对一些导演很崇敬,譬如费里尼、黑泽明和伯格曼。但我不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大师。有太多的导演只是拍了一两部作品就销声匿迹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
B:你在见面会上说过,如果要给年轻导演什么建议的话,就是要“对自己保持真诚”。你认为电影是一种个人表达的艺术,还是一种娱乐形式?
A:两者都是。你必须现实,拍电影的成本非常高。拍电影不可能只是满足自己就行,要让别人觉得好才行。每个人都想被别人赞赏,都不想被别人误解,但你得花上些精力才能做到。拍电影过程中,会花掉很多别人的钱。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有一种要尽自己全力的责任感。但同时,你也要保持真诚。千万不要盯着那些非常卖座的电影不放,千万不要只想着通过拍电影来赚钱。那永远都不会行得通。观众并不傻,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很聪明。他们不会想要被操纵,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动作片也好,喜剧片也好,什么类型的片子都能成功,但成功的电影一定是聪明的。
B:来说说你的新片吧。
A:下周一我要在丹麦开拍一个新片。这是一部爱情片,叫作《玛丽的激情》,根据丹麦著名画家玛丽·科耀的真实故事改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同时,我还准备在今年拍摄《开往里斯本的夜车》。这是根据一部畅销小说改编的,但现在我不能透露更多的细节。
本文转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