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 柏林
——冯塔纳(Fontane)的《艾菲·布里斯特》(通常被译作《寂寞芳心》,Effi Briest)是你计划拍摄的头一部影片,真是这样吗?
——是的,但在1969年,我无法筹集到这笔资金,而今天我为此而庆幸。那时我可能会试图去讲述那个故事,而不是象现在所做的那样只是去拍摄原作。那时我也没有多少经验与技巧,我的影片恐怕会和别人改编的那两部影片没多大差别。有些事情是你不应该一想到就去做的,你应该把它们留待你确实已做好充分准备时再去做。《艾菲·布里斯特》是我梦寐以求的影片,我决定把它拍成黑白片,因为那是我所认为的最为美妙的色彩。这是一部我不带任何杂念,真正渴望拍摄的影片。如果片子赚了钱,那当然好了,可那不是我的目的所在,这也是我耗资极大的一部影片,实际拍摄花了一年多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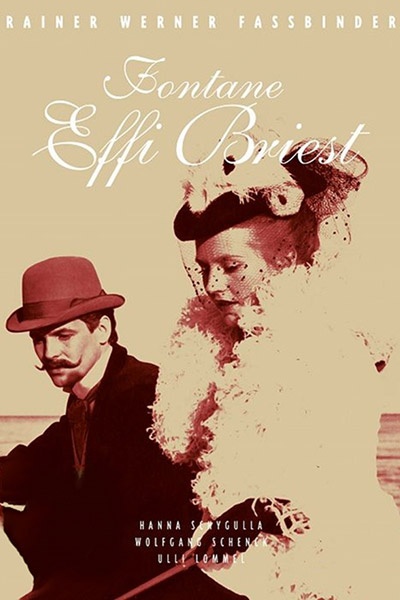 《寂寞芳心》海报
《寂寞芳心》海报——你认为讲述书中的故事与拍摄原著有所区别吗?
——是的,可这区别是就我个人而言的。我忠实于原著……不是忠实于它所讲述的故事,而是忠实于冯塔纳对这故事所采取的立场。当然了,你可以只讲述这个故事(一位年轻姑娘嫁给了一个老头,她不忠实于他,如此这般),以此拍成一部生动的影片,可如果你只是这样来讲述这个故事,那么就大可不必来拍摄冯塔纳的长篇小说。你完全可以自己编一个类似的故事,我拍摄我自己编的与之相同的故事《玛尔塔》(Martha)时,就是这么干的。对我来说,《艾菲·布里斯特》讲的是冯塔纳的社会立场,这也就是我在影片中,通过观众与银幕世界之间的距离再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观众与银幕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东西,可能是原作者,或许就是我这个导演。通过这种内在的距离,观众便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的社会立场。
——怎样看待冯塔纳的社会立场?
——这很简单。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认识到这个社会的谬误,并且能极为精确地描述它,但是这个社会完全是为他所需要的社会,是他真正渴望从属之的社会。他唾弃每一个人,并寻找与之相反的一切,然而他毕生奋斗便是为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而这也是我的社会立场。
——这就是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抨击你的原因吗?
——是的,可不仅如此。或许更多是因为我把近乎他们立场的那些东西极为清晰而准确地描写出来,这使他们感到困扰。
——你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原则似乎与让-马里·施特劳布 (Jean-Marie Straub)的观点有联系,而你的第一部影片又是题献给施特劳布、罗默尔(Rohmer)和夏布罗尔(chabrol)的。请谈谈在你创作生涯的开端,你和施特劳布之间的关系好吗?
——这很难说,因为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很多事已发生了变化。然而,时至今日,由于施特劳布如此异于寻常的严肃态度,以及他依然为即兴创作保有一席之地,我仍然能够承认他与他的作品。施特劳布并不象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固执;固执的一方是他的妻子丹尼尔·惠莱特(Daniele Huillet)。撇开他的执拗与严肃不谈,他工作时也喜欢开开玩笑。他为我们在慕尼黑的“活动剧团”执导过弗迪南德·布鲁克纳(Ferdinand Bruckner)的《年轻人的病态》(Die Krankheit der Jugend)那是一部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话剧。施特劳布逐渐把这部剧压缩成一部只有十分钟的影片,那部短片十分美妙,而且保留了原作的要旨。我们为那十分钟干了四个月。施特劳布的工作方法是:从不对演员说他们对或错,他只是说:“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他用这种方式指导演员从而使他们发现自我,我觉得那真是妙不可言。我对他后来的影片不大感兴趣。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短片《Machorka-Muff》和《新郎、喜剧女演员和拉皮条的》(The Bridegroom,the comedienne and the Pimp),后者取材于布鲁克纳剧作的片断。《不和好的人们》(Not Reconciled)也是一部十分凝炼而美妙的作品。施特劳布的弱点在于他老是要与他的观众为敌。《Othon》是一部我彻底否定的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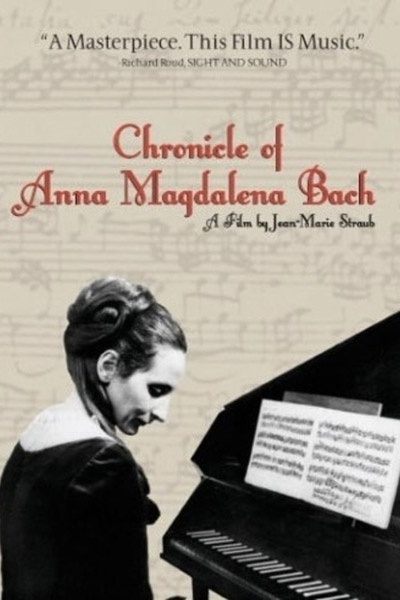 《安娜·玛格达勒娜·巴赫的编年史》海报
《安娜·玛格达勒娜·巴赫的编年史》海报——可《安娜·玛格达勒娜·巴赫的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Anna Magdalena Bach)获得相当多观众的喜爱。
——是的,因为那音乐美。那部片子表现的是施特劳布所听到的巴赫的音乐,这使它客观上具有了某种趣味性。可Othen……
——在这部谈巴赫的影片中有一个原则,我认为在《艾菲·布里斯特》中也可以看到,即:并不呈现那些关键性场景,而只是让人物谈到它们。
——的确如此。假如我们拍摄“行动场面”,我们就会要求观众与人物认同。但事先既经决定不是要拍摄那样一部影片,我们就必须把行动场面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这些场面已经以争论的方式提到过了,在一部影片中呈现叙事因素很象一位作家在讲述故事,但又有所不同。当你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读者创造自已的想象世界,可当一部影片在银幕上用画面讲故事时,这故事是具象的,是真正“完成了的”。做为一位电影观众,你不会是创造性的。我在《艾菲·布里斯特》中试图打破的正是这种被动状况。我倒愿意让观众去“读解”这部影片。对这部影片你不能仅仅去体验,它并不要主动地打动观众……你得去读解它。这便是本片最为显著的特征。
——最明显的例子是你对决斗一场的处理,在那场戏中,你把重点放在导致决斗的那几次争论上,而几乎没有呈现决斗本身。
——一点不错,你几乎什么也没看到。那场决斗是那些人物思索方式妙不可言的逻辑推演。可决斗自身并不那么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这件事作为人物观念产物的存在。本片表现的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某些事件会导致决斗,而这种特定的决斗表明某些重要推论。我感兴趣的是行动段落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对行动场面本身我并不感兴趣。
——实际上,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那些爱情场面——尽管这在原小说中也没有予以更多的描述。人们不知道艾菲和马约尔.克拉姆帕斯是否真的有过性关系。
——我认为他们有过,但这问题是容许争论的。冯塔纳并不曾坚持某一种理解方式:如果你打算把它理解为通奸,那么你尽可以按照这种思路来发挥你的想象;可如果你那种市民阶层的道德观不允许你这样想,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包含性爱行为的爱情故事。在影片中也是这样处理的。照我看来,他们当然发生过性关系。可读者和观众必须在自己的想象中做出判断:这些人物是否可能犯了通奸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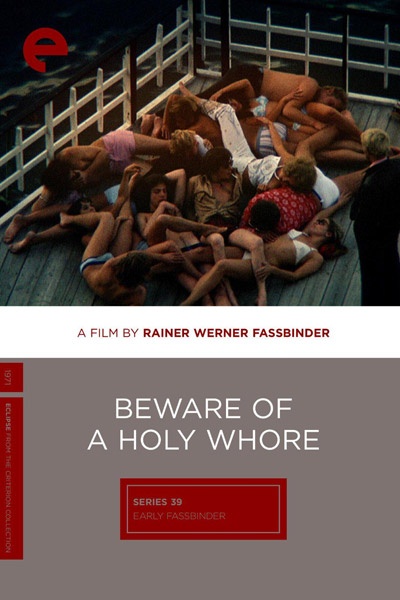 《当心圣妓》CC版海报
《当心圣妓》CC版海报——为什么你对女性形象倾注了这样多的关注?你能肯定自己的态度与妇女解放运动无关吗?
——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只是象非难男人一样评说女性。关键在于,我觉得把女性形象当作主角,能够更好地表达我想传达出的东西。女人更易于冲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被压抑者,而从另一方面说,她们又不完全是,因为她们利用这种“压抑”作为胁迫。男人是如此单纯:他们比女人更平实。把女性当作主角也更富娱乐性。男人的表意方式是原始的,女人则能够更多地发露情感,而这用在男人身上便令人生厌。
——最近你是否看过你早期的影片?今天你对这些作品作何感想?
——不久前,我用四天时间看了二十三部影片,因为有一部关于这些影片的书籍即将出版。在《当心圣妓》(Beware of a Holy, Whore)前的九部影片中,有许多东西我相当喜欢。这些影片对我当时的境况进行了具体的表述。如果你把这几部影片通看一遍,你便会清楚地看出,影片的拍摄者是个极为敏感、充满了挑衅情绪与恐惧心理的人。可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九部片子并不那么对头,它们有着过多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过于个人化,那只是为我自己和几个朋友拍摄的影片……我拍摄出这些影片固然是重要的,但即使对我说来,拍这样的影片没什么错,可从客观上讲,那样做不对头,因为你必须尊重观众,而不是象我在这几部片子中所做的那样。《当心圣妓》看上去可能也是极为个人化的,但这部片子已有所不同。这是一部关于电影摄制的影片,它真正的主题是表现一群人如何一道共事。
——今天看来,这部影片颇为奇妙,显而易见,它标志着你创作第一阶段的终结,而且表达了一种极为真切的自我批评。你拍摄这部影片时,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终结、一个新的开端?
——我并不确如那是一个新的起点,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次终结。我们用那部影片埋葬了“反戏剧”——我们的第一梦。我不如道那以后会发生些什么,可我知道一定会有所变化。
——我认为假如是你,而不是路·卡斯特尔(Lou Castel)扮演那位导演可能会更好……
——很多人都这么说。或许确实如此,但要是我演,影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可以把这个人物演得更没有人情味儿,可那不大对头,因为影片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已经是非难式的了,如果我再把他演得毫无人情味儿,就太过份了。就影片的初衷而言,由我来扮演这个导演似乎要好些,可对普通观众来说,路·卡斯特尔更好。
——你的这部影片和特吕弗的《日光夜景》(Day for Night)都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电影是置身于人们与其生活之间的某种存在。你甚至称电影艺术是一个“圣洁的妓女”,并在片名中告诫人们提防它。
——是这样,可拍电影有一种热狂,它与普通的一天八小时工作不一样。电影联系着一切……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的正常生活便完全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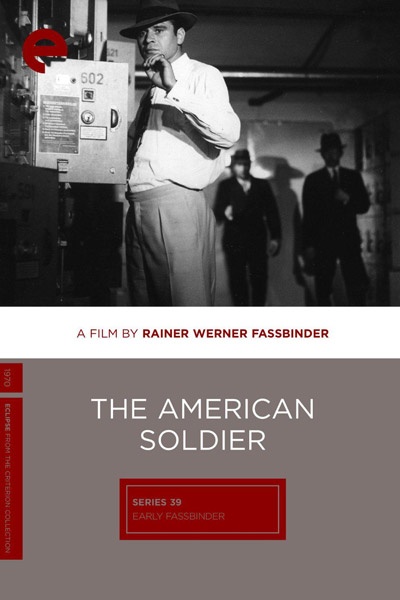 《美国大兵》CC版海报
《美国大兵》CC版海报——和特吕弗不一样,你对“电影比生活更重要”这一观点持批评态度,你自《当心圣妓》之后的影片也都建筑在这一批评之上……
——是的,我仍然在为真实的生活和现实而战斗。
——你重看《美国大兵》(The Amercan Soldier)时,觉得这部片子怎么样?
——《黑死病之神》(Gods of the Plague)比较个人化,可《美国兵》或许是一部更完美的影片。它源于《爱比死更冷》(Love is Colder than Death)和《黑死病之神》,拍得相当凝炼而讲究。前两部影片较为准确地重构了当时在慕尼黑笼罩在人们中间的那种氛围,与之相反,《美国兵》则是一部较为传统的小说叙事式电影,其中充满了取自于好莱坞影片和法国警匪片、特别是拉奥尔·华尔许和约翰·休斯登的影片的电影引文(film quotes)。当时,我在电影中更偏重于阐述政治观点,可现在我认为“电影引文”更为重要。
——你的早期影片使我想起警方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之间的关系……
——那完全是我拍摄那些影片时德国的社会气氛所致,当时我不可能拍摄一部专门讲述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影片,即使在今天我仍觉得那很难处理。克劳德·夏布罗尔在《纳达》(Nada)中所做的,实在是错误百出,那不是一部我所期待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影片。我对夏布罗尔期待很高,然而他就象对社会一样对恐怖分子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真叫我大失所望……他的态度未免有点儿太轻松了。
——为什么你不以此为主题拍摄一部影片?
——那很难办,因为我无法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我能澄清自己的立场,我可以肯定我以后会拍摄一部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片的。
——一方面,你能够理解公众对无政府主义者使用暴力、及其与他们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的行为方式所采取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你又同情无政府主义的境况及他们对我们社会某些方面的批判……
——对极了,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怎么能够利用那些人所具有的力量。现在,拍摄一些十分积极的影片对我说来至关重要,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些非常聪明的人,他们在智能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同时也有一种过于敏感的绝望,我的确不如道怎样才能建设7性地利用这些特点。由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开始使用那些愚蠢的方式,以此与他们不曾真正发挥出的力量取得平衡。他们有着一种可怕的狂躁。他们认为明天便必然会爆发革命,而因为革命并未发生,他们便狂躁不安。人们都不得不以几个世纪来记数世界历史,可他们只考虑几十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能有什么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之所以不能拍摄一部关于这些人的影片的原因。《纳达》不是一部真实的影片,因为夏布罗尔没有赋予影片一种深刻的绝望,而那是这类影片所必需的。我对这部影片不感兴趣,因为夏布罗尔对双方都冷眼旁观。
本文原载于《法斯宾德论电影》
【更多阅读】
《法斯宾德论电影》
《法斯宾德谈<玩偶之家>》
《法斯宾德谈电影中的女性》
《法斯宾德:人们应该有着开放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