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 法兰克福/戛纳
——象《艾菲·布里斯特》和《玛尔塔》这类影片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影片把女人表现为容忍——甚至向往——自己受压迫的人。
——大多数女人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已完全习惯为这种压抑机制所控制。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内心深处不痛苦……她们当然会痛苦。一个人对某一事件做何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性。我认识一些优雅而自由的女性,她们欣赏那种被压迫的境遇,同时却又为反抗这种压迫而斗争。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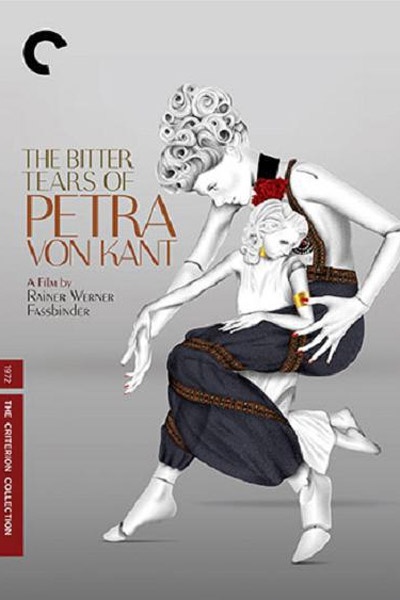 《柏蒂娜的苦泪》CC版海报
《柏蒂娜的苦泪》CC版海报——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异常激烈地抨击《佩特拉·冯·康特》和《艾菲·布里斯特》。
——有些女人的确十分尖锐地抨击我,称我是厌女症患者——这是个我一直拒绝认可的指控,我不是个女性憎恶者,只有那些(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我影片中真正表达的东西的人,才会给我加上这样的罪名。甚至在《玛尔塔》当中——玛塔这个形象由于她的遭遇,以及她以某种方式欣赏这种遭遇,便大大加剧了那种责难——在我看来,这一点也足够清楚了,即:玛塔的反应是建筑在她教养的基础上。根据这一观点,《玛尔塔》和我所有其他影片一样,都是为女性而作,而不是反对女性的。可几乎所有女性都敌视《佩特拉·冯·康特》——至少是那些有着类似问题,又拒绝承认的女性敌视它。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认为我自己对女性所持的立场是十分诚实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女人的行为只不过和男人的行为一样卑鄙,而且,我认为我们已被我们的教养和我们生活在其间的社会引入歧途,我试图用影片阐明其原因,我对这些状况的描述并非出于厌女症的动机。这是老实话。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还不到我来说妇女应该开始解放自己的时候。每个女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出抉择。我所能做的只是指出哪些事情是错误的,哪些事情是她们必须去做的。
——与你对女性的描述相联系,你有时把同类相食或吸血鬼用作一种隐喻。比如说,在《玛尔塔》和你的话剧《燃烧的村庄》(The Burning Village)中。
——那是个天主教图式(motif),这与我的朋友库尔特·拉布 (Kurt Raab)和佩尔·拉本(Peer Raben)有些关系,他们俩都受过天主教的教育。全部天主教教义都建筑在面包和葡萄酒的寓意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之上。我莫名其妙地被同类相食所吸引。这不是一种积极的诱惑,或许倒是消极的。不管怎么说,存在着某种我一直努力挣脱的诱惑,尽管我自己并不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成人的。
我所受的教育与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的理论完全吻合,这种理论不是宗教的,而是建筑在教育学的原则上,它认为不该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情,而应该永远让他们自己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要允许他们做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事,而不强迫他们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这种理论的倡导者想象:孩子们应该象娇嫩的花朵一样成长。
——那这种理论对你合适吗?
——对我来说,就是这种理论也过于强制。我在一个完全没有强制行为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没有人为我的吃、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忧心仲仲。只有当我去拜访邻居或亲戚时,才会体验到那种高压式的强制;我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时,从没有过这种事。我从四岁起,就全权决定自己的一切。所以当我开始上学时,我一点儿不习惯按时或守规矩。我一直憎恶那一套。
 库尔特·拉布,法斯宾德御用男演员之一,也是其同性恋人之一
库尔特·拉布,法斯宾德御用男演员之一,也是其同性恋人之一——你是否准备继续这种令人惊愕的创作速度,还是打算稍加放松?
——有时,我也想放松一下。可同时我发现,工作于我已成了不可或缺的需要。当我没事可千时,我便极为沮丧。就时间而言,我的计划是,当我年届三十之际,拍摄我的第三十部影片。我已经获得了许多东西,那是所有的电影导演们都梦寐以求的,我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更为成功,也比他们大多数人收入都多,但那些东西本身没给我带来任何欢乐。当我看到人们在怎样生活,我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欢乐。当我在街道上或火车站遇到那些人们,注视着他们的面孔和他们的生活,我的心中充满了绝望。我时常想大声嘶叫。
人们经常责难我的影片是悲观主义的。要说悲观自然也有它许许多多的缘由,但我根本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影片。这些影片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革命并不存在于电影银幕上,而是在银幕之外,在世界上。当我在银幕上向人们呈现出事件恶化的情形时,我的目的是要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改变生活,事情将会怎样发展。影片结尾是否悲观,这没关系,只要它能明辨地向人们揭露出,完全是某些机制在发挥作用,那么最终的效果便不是悲观的。我从未试图在一部影片中再现现实。我所追求的是,以某种方式揭示那样一些机制,从而使人们认清改变他们自己的现实的必要性。
本文原载于《法斯宾德论电影》
【更多阅读】
《法斯宾德论电影》
《法斯宾德谈<玩偶之家>》
《法斯宾德谈他的早期作品》
《法斯宾德:人们应该有着开放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