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编译:韦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这样的,再也没有正义、道德可言。回到70年代,你根本想象不到几十年后世界竟会变成这样,如此的市侩、泛滥的暴力,而且毫无希望可言……两相权衡,简直会让人对当初的资本主义百般怀念,至少当时的资本主义还有某种道德形式可言。”
许多欧洲导演都喜欢用电影还原1968年的“五月风暴”,追忆那段满溢着青春激情的岁月。终于,已经57岁的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也没能抵挡住怀旧的诱惑,在具有自传性质的新片 (Après Mai)中,回顾了那一代法国青年在“五月风暴”之后的理想与哀愁。影片于去年11月在法国公映,借此机会,法国杂志 记者让-马克·拉郎内(Jean-Marc Lalanne)对阿萨亚斯进行了专访,重新梳理了他这一路走来的思想发展史,以及对历史、政治运动、电影的看法。

当时我们都觉得五月运动以失败告终
Q:1994年你39岁时拍摄自传性影片 (L’Eau froide),主人公吉尔和克莉丝汀是一对生活在70年代初巴黎的年轻情侣;2005 年你出版了回忆录 (APost-May Adolescence :Letter toAlice Debord);如今这部 再次关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主人公仍是吉尔和克莉丝汀。三部自传性作品关注的都是同一主题,是这样吗?
A :是的,但三部作品关注的程度不同。三部作品的出发点是同一个,但彼此之间并无密切关联。 是文字作品,所以能对自传性内容做深入挖掘,也是三部作品中最算得上自传的。它也是那两部电影的起源,通过这本书,我试着将那个在7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阿萨亚斯,与20年后拍摄了关于那段青春期的自传电影 的那个电影人阿萨亚斯重新联系在一起。当初写下那些文字,令我有机会与那个时代做个了结。到 时,我有意与70年代初那个时期的外在表象保持一定距离,服装、色彩、人物举止行为上都是如此。虽然影片再现了那段历史,但主要是借由朋克乐、摇滚乐这一形式。这次的 ,我似乎已经没有理由回避了,必须从视觉、感官角度忠实再现那个时代。
Q:你是到什么时候才告别学生运动的?
A: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参与斗争。1971年的法国中学生运动可说是自毁前程、无疾而终。各路中学生行动委员会解散后,只剩下学生中的法共力量还在活动。但我们对那些人并无好感,讨厌他们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态度。此外,也有部分学生受到托派运动吸引。而我当时比较接近的是“革命万岁派”,这是个由无产阶级左派阵营分裂出来的边缘组织,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这场学生运动与当时社会上的反文化思潮密切关联,主张万象更新,起初更倾向于青年而非无产阶级立场。我当时则有些同情无政府自发主义运动,倾向于打破一切。不过自始至终我并未加入任何集团,也谈不上参加过什么斗争运动。贴标语、街头涂鸦、印传单,那些行动我都参与过,但并不属于哪个组织,从没正式登记加入过。6个月后“革命万岁派”就瓦解了,学生和左派之间的摩擦也就此不存在了。之后形势愈加恶化,左派宣布摇滚乐、大麻、流行杂志、流行文化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必须与之战斗。
Q :当时你们这些中学生的思想、自我表达的方式,让现在的中学生来评判,可能会觉得太超乎想象了,你觉得呢?
A :我希望他们别那么想。确实,当时那批中学生在政治上十分成熟,即使现在想来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都受到黑格尔历史观的影响,感觉自己与工人运动传统密不可分。现在很难说清楚到底五月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放在当时,我们都觉得它以失败告终,于是觉得自己肩头的担子分外沉重,希望由我们发起的新一次革命能获得成功。所以我们从以往的革命历史中汲取灵感,大量阅读马克思、普鲁东、巴枯宁等人的著作。如今的年轻人早已不再有这种政治历史感了,哪怕是那些十分热衷政治运动的年轻人。

我从未停止过寻找信仰,始终在追求新的形式
Q:如今那些年轻人的斗争运动和当年比有什么区别?
A:以“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为例,他们反对的主要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但他们的口号若放到上世纪70年代的运动环境中,只能算是改良主义,恐怕没人会接受。我们那时候,非黑即白,但这种观念放在现代社会中却不一定适合。所以说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区别,取决于对未来不同的态度。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过去与现在的标准已经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星球上。但我相信,它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记住就在那并非十分遥远的过去,那些年轻人有着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抗争方式,而这种抗争不能简单地以成败盖棺定论。
Q :换句话说,你之所以拍摄本片,是因为你觉得在如今的主流观点中,这场运动被看作是失败的?
A :关于这场运动已经有许多人写过了,我感觉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那就是它失败了。但我要指出,书写这段历史的很多当事人当初都属于左派阵营,他们现在感到后悔了,放弃了自己年轻时候信仰过的东西。
Q:你呢,从未为过去感到后悔过?
A :从来没有。
Q :哪怕是70年代后半段,当你全情投入朋克运动的时候?
A: 那和后悔不后悔毫无关系。我讨厌左派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恰巧朋克乐也对此十分排斥,而且在我看来,朋克乐的蓬勃发展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批判思想和情境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的愿景是完全对应的。是德波的思想令我免于被极权主义欺骗,为此我对德波永远充满感激。左派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意识形态上 的错误容易造成极权主义,出现问题后又容易视而不见,由此导致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政治运动。而我却从未停止过寻找信仰,始终在追求新的形式。这时候朋 克乐出现了,听了5分钟,我就告诉自己:找到了!这就是革命!左派再也无法做到的事,朋克乐都能做到:针砭社会现象,塑造信念,提供能量。在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的音乐中,我明确地找到了情境主义。
Q:你信仰的是德波激进的景观批判理论,但作为影迷和
影评人,你感兴趣的电影却是美国娱乐片、类型片、香港动作片,如何解释这种背离?

A :太年轻的时候接触德波的书,必然会有几个毁灭性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于艺术工作的否定,认为政治行为能超越艺术。能否摆脱这种想法,关键在于对个人主义的认识。关于这种集体价值的衰退,戈达尔在1968年的运动过去十年之后找到一个完美的电影片名: [Sauve qui peut(la vie)]。对我来说,我找到的出路就是选择了电影这种艺术样式,并且发现这里还有意外惊喜:非异化的工作。拍电影的时候,不论你占据什么岗位,都可以出于共同信念而集体劳作,付出自己一部分的努力,获得与他人共同分享成果的快乐。
Q:回看你当年那些评论文章,似乎体现出你某种两极分化的特殊偏好,一边是你对那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封闭式系统的着迷,例如居伊·德波、肯尼斯·安格(Kenneth Anger)……
A:对,还有布列松(Robert Bresson)????
Q :……而另一边则是你对于那种纯粹好莱坞式的电影的偏爱……
A :我信仰电影作者论,但它如今并不受到重视。在我看来,无论是身在好莱坞还是身在非洲马里共和国,真正的电影人所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他拍摄的作品既与电影有关,又关乎他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本就是生活的体现。我之所以喜欢安格的电影,看中的并非是他对抗整个电影世界的激进态度,而是通过他的电影,我得以了解关于他这个人的最新动态,肯尼斯·安格这个人,本就是个最独一无二的主题。在那些开创全新电影形式的伟大导演身上,我们都能找到这种最纯粹的形式:塔可夫斯基、戈达尔、布列松????话说回来,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既然你欣赏的是德波,是布列松,怎么你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却又是现在这种样子的?答案很简单,布列松的电影从来都不会鼓励别人也去拍摄布列松式的电影。它的存在仅仅只是证明有过这么一位名叫罗贝尔·布列松的电影人,他开创了一种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电影系统,他自己却能由此达到当代艺术的巅峰。剩下的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你也得想出自己的办法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表现方式。
Q: 说到你上世纪80年代在
写的那些影评,确实具有某种开荒性质,某些当时并不为主流文化媒体注意的电影作者,都由你率先发掘了出来,例如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电影,在那之前并不受到法国评论界重视,或是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卡朋特(John Carpenter)的早期作品,原本只被视作普通的B级片,还有那些香港动作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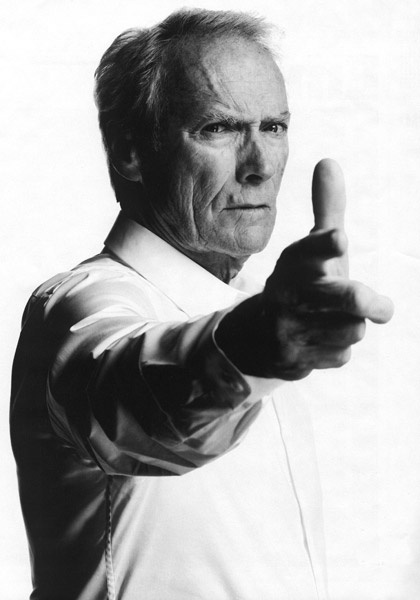
A:是的,我在 时就对卡朋特、柯南伯格、韦斯·克莱文(Wes Craven)这些人的电影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很年轻,有意在视角严苛的传统评论界不去注意的那些领域寻找真正的电影作者。在当时,但凡稍微严肃点的评论家都不会对伊斯特伍德产生兴趣,因为他被看作是右派,抛开这点,他们也不觉得他作为导演的水平怎么样。说实话,我现在对他也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如今的他实在是太右了(笑)。看到他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感到震惊。以前我觉得他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他身上我能找到人道主义,我欣赏他的电影,因为它们承载着某种美国传统的东西,由约翰·福特(John Ford)那里继承而来????可如今的他,竟然与卑鄙无耻的罗姆尼同流合污,真是叫人难以忍受。说来有点恶心,但必须承认,当初第一拨提醒大家“注意了,这是位真正的电影人,但也别忘了,他的作品具有充分的道德复杂性”的人里面,就有我一个。再说到卡朋特、柯南伯格、克莱文这些人,他们的早期作品其实很有力 量,充满了当代性。这在当时也很明显,稍稍挪一下角度就能发现,可惜大多数人死抱着传统价值观不撒手,没能及时注意到。我始终觉得,尽管是恐怖片,但只要 我能从中发现某些造型上、感觉上让我产生兴趣的东西,恐怖片也完全可以是旷世杰作。我之所以热爱美国电影,欣赏的就是它关于人类身体的那一面,美国电影很注重针对人体本身制造各种效果。
面对种种革命企图,当今社会早已有了更好的防备
Q:当初对于政治运动的全情投入,如今对你来说是否还留有什么影响?
A:如今影响我的,其实并不是我发生在70年代的青春期,而是我对80年代、90年代的了解与认识。我亲眼目睹了这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这样的,再也没有正义、道德可言。回到70年代,你根本想象不到几十年后世界竟会变成这样,如此的市侩、泛滥的暴力,而且毫无希望可言,但这确实就是如今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环境。资本主义本身,也从70年代我们所了解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如今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两相权衡,简直会让人对当初的资本主义百般怀念,至少当时的资本主义还有某种道德形式可言。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如今我又回过头重新审视当初接受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70年代,我受到德波、阿多诺(Theodor Adorno)、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习惯了从高处审视左派,觉得他们的想法有些笨拙,但随着时间流逝,如今反而觉得自己和左派观点更贴近了。
Q:你对诸如巴迪欧(Alain Badiou)、齐泽克(Slavoj Zizek)、内格里(Antonio Negri)这些人现在的观点有何看法?
A:我觉得,面对种种革命企图,当今社会早已有了相较过去更好的防备。体制对于激进言论有着很好的吸收作用,它有足够多的防撞气囊,随便你如何声嘶力竭,都产生不了多少回声。 (The Dark Knight Rises)也好, (Matrix)也罢,它们都成功消化了大量的批评声,结果毫发无损。凶猛的批评来自各个角落,但都产生不了作用。好莱坞就是有这种本领,吞噬各种激进言论,用它的“共谋犯酸奶”将之稀释,再将所有问题搞得一片混沌,让你一点想法都没了。面对这种情形,所有观点都如石沉大海,白费工夫。但我们还是有可能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找到希望。例如Pussy Riot那几个姑娘,仅仅只是三个女孩子,却能让普京为之犯愁。即使把现如今所有思想家的激进批评言论全都集合在一起,也没有她们的力量大,没有她们的冲击力强。 这才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也让我们重拾信心,相信少数派也能继续投身革命,也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