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0年3月15日
参加人员:田壮壮、简宁等
背景:
田壮壮于1998、1999两年间9次下到云南中滇、怒江一带民族边远地区采访和考察,筹拍关于云南茶马古道的系列纪录片电影。
2000年,其中第一个单元《马帮》的样片完成后,笔者有幸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室观看。当时应《母语》杂志之约,笔者就此主题与田壮壮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本文曾发表于《母语》杂志2000年5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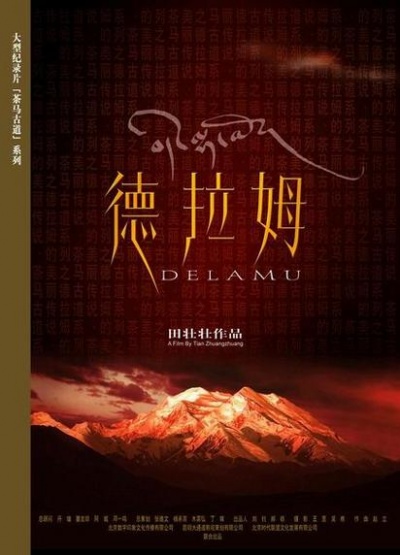 《德拉姆》电影海报
《德拉姆》电影海报简:怎么想起来去云南拍纪录片的,这个动机从哪儿开始的?
田:我的第一部电影《红象》,就是在那里拍的。(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一些原始的民族……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想再拍一个故事片,表现那个环境里几种文化的碰撞,你看——(云南那一带)有中原文化,从汉开始的历朝历代,基本上控制着云南的整个地区;当地的土著文化,就是本民族的自身文化;从印度或西藏过来的佛教文化;还有西洋来的基督教文化……这几种文化在一起,为什么能够那么和平、(彼此)融合地保存下来?我认为,哪一种文化符合人类、人性的发展规律,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哪一种文化就会表现出它的生命力,得以流传和光大……当时就想拍这么一个故事片,那是1980年。
简:20年!那为什么没拍?
田:我很多年没去。很多朋友都是捶胸顿足地想去,但都没去成……
简:为什么?
田:环境问题啊,交通问题啊,费用问题啊……最后一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北京这边的文人还是很少有人深入到那里。所以拍云南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简:这是你这次拍片最原始的动机了?
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益于儿子对自然生物的爱好,因为云南在中国是昆虫蝶类的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他一直跟我说想去,前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带他去了西双版纳。虽然隔了这么多年,云南的生活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某些东西,人们的生活方式啊精神状态啊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样又勾起我18年前的情结……
我们去了一个老教授家,是研究云南民族分类、民族史和编纂云南志的,姓木……他儿子(后来成了)这次拍摄茶马古道的主要干将,叫木霁弘。小木是学语言的,通过语言调查来研究各个民族迁徙和演变的历史,他给我带来一本他写的书,叫做《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这本书里就写到6个年轻学者自费去考察茶马古道,他们6个人基本都是学语言的,无意中对古道产生兴趣,开始沿着这条古道来考察——他们并不是要考察马帮——还是考察语言流变的,但是这条路的兴衰深深吸引了他们,从书里也可以看到,他们被沿途当地的文化、历史、人文状态所震慑,基本上这个东西已经不仅是一个学术成果了,完全是心里的一种赞叹和感受。他们觉得:喔,这世界……!
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挺受震动,他们作为语言学者,选择这么走,在走的过程中又把专业的事完全抛开了,而对另外一个现象产生兴趣,非常有意思,所以没过多久我又回去专门找他们聊……
简: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拍摄构想吧?
田:没有,只是找他们聊……小木教授详详细细地跟我讲他们走的经过,搜集了几百盘民歌民谣的录音,拍摄了上万张照片。我感觉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题材,后来又跟阿城说了……阿老跟我聊的过程中就慢慢确定了把茶马古道作一个纲领来延伸它的内容和题材,各种文化在这里这么融洽地融合,必定隐藏着有趣的秘密。于是我就找一些朋友谈,有些投资人对这个事非常感兴趣,大家聊到这儿就决定做这件事了。由我先到下面把这几条线都跑通,先感受一下。这一趟实际上只跑了怒江一线。
简:也就是说所谓茶马古道还不只是这条线?
田:茶马古道在中国的运行范围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等地,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进一步还涉及到另外一些国家。要说线路嘛,以西双版纳、思茅的勐腊、勐海、澜沧江流域为中心地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大理、剑川、鹤庆、丽江、中甸、德钦、左贡、察隅等等;从剑川沿三条江的江边一直往西藏方向走。三条线实际上都在大三角的西藏境内汇聚,路途都不算太遥远,但都在崇山峻岭之中。沿江走主要是由于住民都住在沿江的山上。
简:这些商路有什么记载吗?原始的开发者在历史文献上重要吗?
田:重要!关于茶马古道的资料,实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张骞在大夏见筇竹及木棉布,得知有一条商路从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张骞被囚十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的情况,由此引发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雄心,于是派遣四路使臣前往云南寻找“身毒道”。不幸的是使臣纷纷受阻或被杀于滇部落。为讨伐滇人的悖逆,汉武帝在长安仿云南洱海外形开凿昆明池演习水兵,从此云南历史上有了“汉习楼船”的故事。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大量饮茶,古道又恢复了(它的喧嚣)。唐人樊绰《云南志》(又名《蛮书》)详细记载了滇茶入藏的路线。随着茶叶为载体的商贸日趋发达,宋、元、明、清大大强化了这条道路,由此形成了亚洲大陆最为庞大复杂的商业道路。
可以这么说吧,茶马古道扎根在亚洲板块最险峻的横断山脉,她维系着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和汉文化集团;她分布在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滇、川、藏及东南亚和印度文化圈上;而且最重要的,茶马古道或许也是亚洲大陆上惟一一条还在运转的文明古道,至今还在发挥着活力……这些林林总总大概就是你说的拍摄的起因。
简:你已经九下云南了,那么这一次是不是体会更特别一些?
田:这次去怒江以后比前几次跑深入一点,到老乡家,跟老乡直接对话了。这些人才是元气十足的,活得很安宁……
简:你是不是一直有人类学的兴趣?
田:人类学嘛,我觉得有点大了……我自己不是一个……
简:人类学工作者?
田:不是一个学者。我挺知道自己的,任何一个项目或主题,我进入得都不系统,都是那种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东聊一下西聊一下……我还是对人有兴趣,对人性、人的生活有兴趣……你想,我是拍电影的,不拍电影实际上挺难受的,但是我这个性格,拍现代的故事片,像市场那些,不是特别合适。我这人比较率直,喜欢的东西可以玩命干,不喜欢的东西你让我憋着性子拍,也不可能拍得好。
中国电影三座大山,一个是电影生产体制,管理、市场,包括审查机制都有问题;第二座大山是经济,我刚拍电影的时候,20万、30万拍一个,现在200万、300万都不一定拍得了;第三个就是自己,创作人员,创作者拍出一部电影并不难,但是拍出一部能够超越自己的电影却很难。
我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再这么拍电影,组织者本身就犯了渎职罪,比如你投入了300万,收不回来,那钱是国家的啊,所以也就是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是?
我不是搞理论的,想的都是一些直觉的东西,但是我想到这些问题会感觉挺可怕——电影的走向,电影的发展,我们没有力量去扭转乾坤,也不可能独撑一臂,但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点的事就可以了。为什么想拍纪录片?前天北影厂艺委会讨论剧本时我就说,经济改革以后这些年我们把“深入生活”这四个字给丢掉了,觉得是迂腐的东西,现在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屋里编,这么编剧本的话不如学好莱坞,用电脑来编,我要多少个起伏多少个情节,10个人编这个故事肯定比1个人编的好,因为你不要生活了嘛。你去观察世界所有经典影片,没有一个不跟社会、不跟人、不跟真正的情节、细节打交道,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灵魂也没有肉,不可能成为好电影。
我也渴望拍故事片,但我希望能在云南做两三年,那样会充实很多东西,就是咱们讲的充电。咱们在城里呆得太多,这一个圈子,我、你、静之,经常在一起聊,这些人可能在一个局部都是精英,但这些圈子会慢慢凝固,非得有新的精英进入的时候才有新的话题。人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一个自然退化自然老化的规律。
一个有号召力的人,比如大导演,为什么有号召力,因为他是金字塔的尖,要有一个塔来支撑这个尖,不能悬着。问题就在于这尖,最容易钝,尖一钝,不锐利了,虽然形还在,但力量感没有了,而尖是需要去磨的,才能保持锐度。这磨就需要外来的刺激,就是社会生活,周边所有的人。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象牙塔里,可能做出这样那样奇观的东西,但没有价值和意义,对文化的延续光大不产生作用。
我为什么不拍故事片?有很多因素,作为我自己,我渴望多交朋友,蜕变自己,能够在真实生活里找到一些自己奇观的东西……
 田壮壮
田壮壮简:真实地发言?
田:记录下来或整理下来,这对我个人有意义,或许有人会说你他妈不务正业,你整理这干吗?没有人要看!有可能,但让我激动的东西一定有让我激动的原因。
简:艺术家必须相信自己的人性,我的人性就是所有人的人性。
田:有道理,这话精辟!(讽刺地)来,我得记下来……
简:你拍这个东西,除了对云南的兴趣以外,还有跟你对纪录片这形式的兴趣有关系?
田:在新中国和旧中国的电影史上,纪录片是比较空白的。
简:纪录片的空白肯定对故事片的市场应该也是很有影响的,包括观众和导演、电影作者本身……
田:故事片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梦幻世界,当人们入世生活的时候,是如此之现实、之冷漠、之残酷,其根本是为了生存。故事片的产生虚拟了另外一个世界,有爱情、悲剧、各式各样的东西,但它是虚拟的,它给入世的人一个真空的时刻,暂时释放和宣泄。阿城把它形容为“深度催眠”。
当前的故事片市场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空间。电影的产生,最大的作用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叙述语言,音乐、文学、舞蹈、戏剧都是一种交流语言,电影是一种新型语言,一个镜头拍一只狗,再拍一盘食物,狗头朝着食物,你知道那狗想吃东西,要屁股朝着食物那是吃好了……这已经不用说了,约定俗成了。一推门,外边是什么,可能从中国到了墨西哥,出去了……
简:你这么说,是我听到的最亲切的电影课!
田:这种语言已经形成了体系,包括现在的电视转播。到现在发展到网络上的语言,有文字有画、MTV,等等,其实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语言(体系),这是这100年出现的人类的新的语言,新的交流方式。这是电影伟大的一面。
纪录片更多地是利用这种语言来介绍一个真实空间而不是虚拟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分别。其实你说纪录片真实吗?它不真实,它不是绝对时空的,绝对时空就是咱们俩这么聊,这边一台机器放着,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三小时就是三小时……
它的语言魅力就在这儿了。它可以组接起来,很迅捷地就让你完整地接收了信息。纪录片是用电影语言来介绍真实时空,你没有这个经验,你马上可以感受和认知这个经验……也有很多揭露社会的故事片,比如美国有很多暴露内部黑暗面的电影,但实际上它都是在一个虚拟的状态中。真正的纪录片抓住一个拍摄对象的主体。而故事片的主体是观众,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进来掏票子我就舒坦了,对吧?所以我就像变魔术,今天是大变活人,明天是空中钓金鱼,后天是烧火,反正总归是要让你进来掏票子……
而纪录片可能在拍摄构想、拍摄过程中都没有考虑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比如考古啊,宗教啊,你说有多少人关注?但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轨迹,这环不能断,就像你说猿人到智能人这中间的环断了,永远你也说不服我,你说我是猴变的,你得告诉我这中间是怎么变的,为什么现在这猴就不能变成人?这链环一丢就有问题了,所以老有人去干这样的工作,一会儿破译玛雅文字,一会儿研究埃及金字塔……做这个事情的人,需要更耐得住寂寞,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
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作为作者,也有这种分野。而且故事片的浮华程度,越来越变本加厉。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和世界的接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关注会给很多人一种梦想,如何如何……
简:一下到塔尖上去?
田:非常有可能。再一想,光着来光着走,尖又怎么着,(即使)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尝了……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可能去过最好的地方,吃过最好的东西,睡过最好的女人,没有他不能做到的,但恰恰有一点,他得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他心里最需要的。他可能没去过真正最美的地方,他去过的是最模式化的地方……最有生命力的东西,(用)他那个钱能不能达到,(这)很成问题,为什么很多挣了大钱的人还觉得苦恼、无聊,钱那么容易挣又那么容易花(掉)?他的生命的驱动力已经变成了一个循环体,他要无休无止地应酬、维护、捍卫,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把他生命中最原始的勃发的动机给疏离、泯灭了……生命的意义太丰富了,人活一辈子,我就希望看到更多的原生态的人,不是克隆的,不是经过制造的,元气十足的它给你生命活力的东西。我在云南山上看到两个老太太,一个102岁,一个98岁,两个人坐在一块,穿得很破,也很脏,你坐在那里看她们就喜欢啊,一点不觉她们很穷\很苦……她们与环境融为一体、游刃有余的那种神韵,对外界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简:回到我们的话题上,你觉得纪录片与专题片有什么区别吗?
田:好多专题片有点像政论片,对某个事情发表一个态度。一个贪污的事件、一个毁林的事件、或者一个环保的事件,可以拍一个专题。而纪录片更多地依照原始的拍摄对象,慢慢观察周边的气氛,自然的气场,表达人的喜怒哀乐,生存的状态,纪录片可以没有政治观点,很多纪录片的观点很冷淡,比如探险的,动物世界的,水下世界的,你也可以有一个主体,比如跟着一个考察队,一个考古学家,但没有故事片里的那种人物性格发展的线索……很多人沉溺于纪录片的原因也是在于他有一种快感,他操作起来不被任何东西所束缚,他自由了,这自由实际是人最本性的东西。在中国有好多拍纪录的好手,问题在于他们可能拍得太真实了,太尖锐了,找不到一个播放的市场。相反过来,我们感觉到中国没有纪录片市场,没有地方播,也没有地方看。
简:国外的电影院里放纪录片吗?
田:有一些。国内的这种状况就变成了对纪录片的成见:那东西没故事,慢条斯理……纪录片,我也是刚开始去感受的。我这次下去回来就念叨,我还是拍故事片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要过三四天才反应过来,哎,那东西当时怎么没想到去拍啊?当时怎么没有往下走一步啊?
简:思维还是不一样?
田:有个过程。在敏感性、对象捕捉的概念上,你还是有一个习惯。我要到那里去搞什么,我还是有一个策划,一步一步走,策划之外的东西你就不留意了。转回来一想,那些东西正是你策划区域里的,只是你没有认识到。一块好石头,雕成玉,你认得它,是石头的时候你不认得它。这次下去,这种情况很多……茶马古道上如同云南大地上的一条褶皱,当人们将她抚平的时候,才会发现那里有着人类上千年的文化记录。
简:是不是说,拍纪录片的时候,即兴和随机性的可能更大更多?
田:你看到那些东西,不是一定真要拍,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了,认识它,当你认识它以后,后面可能有一个无限大的故事。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遇不到这样的故事,因为有很多具体的东西你都可能感兴趣,比如民俗的东西,再如老年化的问题、妇女拐卖问题、衣食不足的问题等等,你不一定去拍,但你应该了解和采访,认识了每一个局部你才能更好地掌握全局。
那天我们开车走着,看见一个土坯房子队部,所有老乡都坐在那里,问干嘛呢,说是开会分衣服呢,当时谁也没在意,我回到小镇的旅馆时就有点后悔,起码应该听听,他们怎么分这几箱衣服,每年来多少衣服,衣服怎么到这儿的……后来我才发现我以后拍摄的人群里每个人都有这种扶贫的衣服。老乡他们自己怎么看这问题呢?心里是什么滋味?比如城里人交往,给你一件旧衣服,你会觉得没道理,给你一件新的你还看喜欢不喜欢这样式呢,那对这些老乡来说在衣服穿着上就有一个对比,这对比会反衬他们的经济情况和心理状态。
实际上人是非常渴望交流的,比如有关语言,完全可以做一个题目拍纪录片……(再比如当地)流动人口的进入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公路,没有公路就不会有这些现象。我在贡山住的时候,他们法院的院长就跟我说,在没修公路之前一年办不了20个案子,现在修通了公路,一年有200多个案子……你就想想,当文明一旦进入原来安静的地区,会引起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关于公路,你可以做出无数个调查报告——案件是一个,人口流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有了公路,你这块的资源肯定丢失。
纪录片这东西,说起来看人家拍觉得不难,但一真正做起来……对我来讲,除了它是另外一个模式之外,还有就是我的准备够不够充分,够不够进入拍摄状态,这是(另)一个挑战。
简:那现在你已经做过的工作还只是一项工程的序幕或者前奏。
田:如果我要拍的话,最少还要两到三个月,做比较细致的采访。想做成一个个单元,各个方面。
简:你现在对下一步的继续拍摄有什么计划吗?
田:我准备了一些,但还都不够,还需要落实和完务,落实到哪一家、哪个人。当他已经熟悉到不对你感到新鲜了,你才能开始拍……